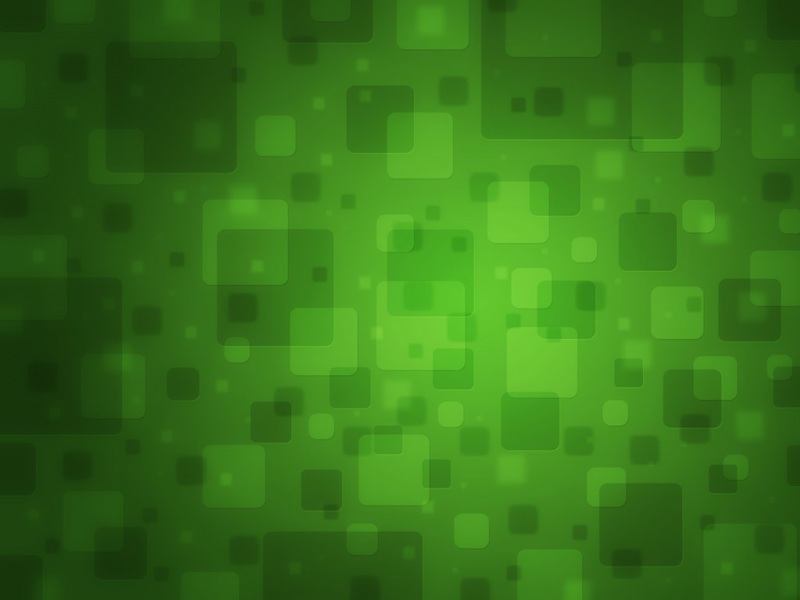记者的经历让我善于提问,但克伦人教会我如何放弃询问,像水一样融入村庄。
文、图、视频 | 伍娇,编辑整理 | 他者others
泰北高山上的克伦村
十月的清迈,白天依然炎热,直到群山把夕阳拢在怀里,空气才开始夹杂些许凉意。我参加“行动源中国-东南亚可持续生活青年计划”,到泰国克伦族(Karen)社区研习已经三天了。但我几乎什么都没干成。
我的辅导员P’Kwiv(P,哥哥或姐姐,泰语中对年长同辈的尊称)是清迈“返乡青年网络”的领袖之一,生活的村庄叫农岛(Nongtao)。这里美丽恬静,坐落在泰国最高峰因他暖山 (Inthanon)所在的群峰中,聚居着三个古老的大家族,大约有160户人家,有七百多年历史。
Kwiv的家很大,在农岛村最北边,面朝一片碧波如倾的梯田和莽莽重山。
穿过热带植物构成的天然篱笆,是大片的草地,他和父母居住的克伦族传统斜顶大屋矗立其上,现在我也住这儿,正对着一座高脚谷仓和放货车、农机的凉棚。踏着草径再往里走,迎面有扇很像日本鸟居的木架,绵延旺盛的食物森林呈现在眼前,抬头有高大的椰子、香蕉、酸角和牛油果,底下生长着青梅、木瓜、柠檬、咖啡……佛手瓜攀上了柿树,树荫下能找到生姜、芋头、蝶豆花和许多本地香料。我想象不出比这更富足的景象了,其间还分布着几间竹木结构的储藏室和会议屋,尤其漂亮的是有透绿玻璃格窗的厨房和开放式咖啡屋。
我喜欢这些可爱的小屋,自然的材料、传统跟现代结合的设计,处处透露出主人的巧思和灵光,人在其中行走坐卧,无不怡然舒适。Kwiv更像是个日式匠人。
放弃计划,忘了时间
初来乍到,我就迫切地想和他聊聊关于这些建筑,可他几乎不会说英文,我们根本无法交流。这是当头一棒。另一方面,作为辅导员的他让我在家里自由玩耍,不安排做任何事。他以种植和烘焙有机咖啡远近闻名,但现在也还没到咖啡豆的采摘季节,它们自由地长在森林里,不用太多照料。我每天做的事就是被热情招待以源源不断的手冲咖啡。
我尝试用翻译机简单的提问:“我们今天要做什么?”“sbay-sbay。”“明天会做什么?”“sbay-sbay。”“后天有什么计划吗?”“sbay-sbay。”
“sbay-sbay”大概是Kwiv的口头禅,它可以是所有问题的答案,也成了我来泰以后学会的第三个单词。前两个是生存必备:你好和吃饭。sbay-sbay的意思“休息放松、慢生活”。
本来我期待着从事的各种有机耕作工作一概没有,加上无法交流,身处异乡异文化之中的我觉得彻底失控。
这情况持续了两三天,午后村里很安宁,都是杆栏式斜顶木屋,间隔宽阔,阳光洒在庭院,狗儿在树荫下玩耍。这样的环境更衬托得我心如鼓击。一切都毫无头绪,村子是什么情况,有哪些传统智慧,甚至去哪找到一个会说英文的人我都一无所知,只能等Kwiv突发奇想。
有一次他终于带我出门,本打算去一个亲戚家拉几袋稻壳,混合家里的红泥给咖啡屋的竹编外墙敷上一层,抵御即将来临的寒冬。不料路过一户人家,我们就被叫了进去, Kwiv和主人长时间地商量起聚会的事(这也是我之后才知道的,当时一脸懵),然后又拿起身边桶里的黄鳝逗家里孩子,幼稚的行为重复了数次;我们好不容易才回到院子,Kwiv的妹妹又来找他去谷仓后赶蛇。我心里无奈地怀疑敷墙的事今天还有没有时间干了。
事实上,这样的情况总是不断发生,克伦人随性地活在计划之外,对我这种不会变通、执着于秩序的人来说简直是折磨。就好像我们身处同一个空间,但活在不同的时间里。他们没有时间观,或者说有一套自己的时间观,不同于现代的刻度系统,叫人想起结绳记事的远古先民,也让人无所适从。
可除了接受,我毫无办法,只有放弃抵抗,就像Kwiv 说的“sbay-sbay”,中文应该翻译成“随波逐流”,或是“乐天知命”?
终于,在我抵达克伦村的第五天夜晚,Kwiv带我到邻家社交聚餐。抵达时屋子里已聚满了村民,这也是我第一次见到这么多人。克伦族传统没有桌椅,大家席地而坐。窗外的芭蕉叶阔如扇,洗浴过的妇女们包着白头巾、穿着水红色的手织长裙,靠着木栏休息闲聊。男人们相互传递“本地威士忌”,也就是自酿米酒,小酌起来,“女士威士忌”则是自酿的梅子酒,通常在席间才喝。Kwiv指着其中一个笑眯眯一脸和气的阿叔,告诉我这是他父亲,就丢下我去做饭了。
我们虽然生活在一起,但当时农忙,Kwiv家又常有客人,人来人往,加上语言不通,他从来没向我介绍自己的家人,那天早上我按捺不住,略带愠怒地问他为何如此,一周下来我甚至不知道他的父亲是谁,不料他竟记到现在。
阿叔一脸莫名其妙,但还是招手让我坐到身边。Kwiv做的是黄鳝,他没有去掉头和内脏,而是直接切成小段放入涨水,然后舂碎香茅、姜黄和一些我从未见过的新鲜香草一起入锅熬煮。“Na,”Kwiv的父亲指向远处告诉我,比划半天我才明白是“稻田”,泥鳅是水稻收割前放水捉来的,还有小鱼和螃蟹。“tamaqiai,”叔叔强调,“自然”的意思——没有农药化肥的污染,田里的物产丰盛健康,这是“稻米人的幸福”。
克伦族的饮食结构非常多样,有大量野生动植物,像是蘑菇、蝉蛹、水草和各种野菜、野果、野花。更值得赞赏的是,他们对食材的处理极其简单,喜欢保留完整食物,很少切割剔除,也没有复杂的加工,多是和香料一起炖煮,也有很多生食。做一顿饭的时间大半花在准备香料上,一遍遍细细舂捣,这对快节奏的都市人来说简直奢侈。Kwiv做的泥鳅很快端上异域风情十足的草编餐席,尽管这对他们来说就是日常餐布。大家围坐过来,浓厚的香料散发着诱人的辛香气息,金黄的色泽令人胃口大开。
这也是我在村子里的第一次社交亮相,很快有人询问我的状况,“where are you from?” 有人越过邻座和我说话,一口流利的英语,周身散发着旧式贵族青年的气质,与众不同。他是Oshi,高中毕业后没有选择大学,而是独自去印度游学,最远抵达喜马拉雅山,之后也去过纽约、东京这样的国际大都市,不过最后还是选择回到农岛村。“Lazy,”他解释自己生性懒散,不过眼神里分明透露着智慧的狡黠:“我们的祖先并不把自己叫克伦人,这是外来者给的称呼。我们自称‘Pakeryaw’,是‘人类’和‘简单’的意思。现在的人都太忙碌了。”后来我才得知,他是家族现任族长的独子,是下一任传统灵性信仰的守护者。
在部落里交际就得靠吃饭,这下不仅和大家混了脸熟,还找到了重要的信息报道人。我问Oshi住址,他指了指树林后面,告诉我就在隔壁,Kwiv是他表兄。这下我心里终于有了些许踏实感。
不去问怎么做,去追踪身体本能
第二天天气很好,Kwiv一早把遮阳帽、手套和长胶靴放在我门前。
我们骑着小摩托出村,村子四周被几个大型国家公园包围,晴朗的日子可以看到泰国最高的因他暖山。在宽阔的公路上行驶一段,Kwiv拐进一条颠簸的土路,最后停在一座高大的凉棚前,旁边已停着许多摩托。转头张望,一排低矮的树丛下是个和缓的山谷,金黄的稻谷散发着成熟香气,三四十个村民在里面,说话声像热浪般喧嚣蒸腾。每人都戴着遮阳帽,有人拿着镰刀,八九成群,正在收谷。
我从未见过这么多人一起干农活。想起过去几年在中国西南山地游历,一位瑶族老人曾告诉我,“几十年前村里人多,大家总是一起劳动,比现在快乐得多。”那些逝去的旧梦在此依然存续,如此珍贵。
和国内不同,克伦人收割后并不马上脱粒,而是扎成一捆一捆,放在水稻残根上晾晒。为了提高效率,通常是两人配合,一人在前一人在后,一人收割一人打结,难点在后者。无法用语言沟通,Kwiv就割下一束稻谷向我演示,我仔细观察他的每个动作:左手略微松开握紧的稻束,右手从中抓扯出夹杂的稻叶,把叶尖放回稻束和右手掌心之间,一起握紧,左手抓住叶尾从下往上缠绕,等到只剩一截尾巴,便轻轻一扭,把它从稻束底部穿过,同时用力一扯,只听“刷”的一声,稻束才算绑好。
要学这个活计,能不能有共同语言不是重点,它是件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事,必须依靠自己的身体感受来积累经验和肌肉记忆,而且只有做到恰到好处才能成功,不然稻束就会自己散开。
第二天起床时,感觉身体不是自己的了,不过还是拒绝了Kwiv“呆在家”的建议,和Oshi、他的爱犬、一头被装在编织袋里的小黑猪,坐着皮卡去到Kwiv父亲拥有的遥远农场——它占据着一整个山谷。
田里几天前割下的稻谷已晒得焦黄,山脚的凉棚里堆着四面半人高的稻墙,中间铺着一张宽大的胶布。Kwiv的母亲拖出小黑猪,割开喉咙放血,装满一碗后递给Kwiv的父亲。他将血倒入一个铺有树叶、装着一抓白米的竹编漏斗形器物中,嘴里念念有词。克伦族传统信仰万物有灵,这是向谷神表达感激、祈求丰收的古老仪式。
Kwiv的父亲找出一块木条钉的长板,放在胶布正中,然后拿两根被粗绳系在一起的木棍,平摊在地面,接着抱来大捆稻穗放在绳上、拿起两根木棍,左边往右边一扣,就像剑客一样帅气地把稻穗提了起来,径直走向长板、双手举过头顶向下撞击,只听重重的一声,金灿灿的谷粒在逆光下哗哗掉落,扬起一阵雾似的尘埃。
民间工具的巧妙真叫人惊叹,仅用两根木棍和一根粗绳就能做成机关。配合长板的好处还在于可以五六个人同时打谷。场地够大还可以不断加板,相较于沉重的谷斗灵活许多。
看我一脸跃跃欲试的样子,Kwiv的父亲热心地给我找来小一号的竹棍——那是专门给女人和小孩准备的。但我很快发现自己的打谷声总是远不如别人响亮,是因为力气不够大?但这里的女人孩子也一样打谷。
语言障碍重重,我不得不放弃询问如何做到正确,这也逐渐让我更多的用眼睛观察。
克伦人打谷时,左手的位置一直在变化:提起稻谷时位于木棍前端,上举的瞬间迅速下滑,至最高处时已和下端的右手紧靠,待到身体前倾,就可以利用稻谷本身的惯性顺势下沉。这样稻谷越重,惯性越大,打得越干净,还省力气。打完这下提起来,双手又回到一前一后,这时位于后端的右手微微下按,又带动木棍抖落还未完全脱离的谷粒。这又用到了杠杆原理,非常科学,我心里啧啧赞叹。随即又觉得好笑,我这样一一分解,可对他们来说却是再平常不过的身体本能。优美沉稳的姿态本身,彰显着土地和人交融的荣光。
为什么不用机器
“都是人力啊?为什么不用机器?”我把收谷的视频发到朋友圈后,很多人发来疑问。言外之意大概是人力效率太低,快用机器吧,会轻松很多。
我想知道克伦人是怎么看待这个问题的。
“我们可以互相帮助,就像现在,每天在稻田里见面、聊天、互助,这对克伦人来说非常重要。”Oshi回答。不过我有点不相信,一边捆稻子一边继续盯着他,这个理由太浪漫了。“也许是因为我们有足够多的人手。”他退一步说,Kwiv的母亲就有七个兄弟姐妹。“你准备养几个小孩?”“我喜欢丁克。”“那以后就没有足够的人了,而且现在年轻人都去外面学习、工作了。”“是的,轰隆轰隆,”他调皮地用手模仿拖拉机行驶的样子,可语气里压抑着复杂的情绪:“也许在不久的将来,机器也会占领这里。”
正是因为现代化的影响、许多年轻人外出,使得Oshi和Kwiv成了最后拥有古典爱情的那一代。稻田是社交之地,他们也在割水稻时谈恋爱,男的割,女的捆。如果男的心里喜欢这个女的,给她的就很好捆,不喜欢就割得很短很难捆。老人看到两个年轻人情投意合,也会撮合他们去远离人群的田里收割,两人互相喜欢,割很长时间也不觉得累,心里只有欢喜。Kwiv年轻时很多姑娘都想和他一起收水稻,他心地好,割得也好。弄得他也不知道是因为喜欢他,还是只是因为他割得好。
“机器需要花钱买,还有汽油,村民之间的互助是不计报酬的,而且我们必须互相帮助。”我向Kwiv抛出为何不用机器这个问题时,他给了我这样一个比Oshi现实得多的答案。相对于国内不足五亩的人均耕地面积,农岛每家每户都有几十上百亩耕地。Kwiv家就有三个农场,每个都有几十亩,单个家庭难以应付。虽然他总是对我说“sbay-sbay”,但他其实一点也不轻松,每天都要去不同的人家帮忙。
更让我慢慢生出敬意的是,和很多人搭档之后,我发现和他总是最熨帖的:他会把稻束割得整整齐齐,回身时以最好拿的角度给我;我绑得慢,赶不及他割时,他就停下来自己绑一束等我;我做错时也从不打断,而是把正确的样子展示给我看。时间久了我逐渐意识到,虽然Kwiv从未在语言上表现,也无法表现吧,但其实一直观察着我、平等地为我着想。
“有的田淤泥有半人高,用机器也不方便,”他微蹙眉头继续补充说:“如果你想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应该询问遇见的每个人。”
后来我又问了他的妹妹,她面露困惑,在她看来这是理所当然的事:“几百年来一直如此,这是我们的传统。我们也不希望用机器,互帮互助、每天见面、交流,比什么都珍贵。”翻译机上显示的内容和Oshi的浪漫答案如出一辙。
我真正开始接受这个答案也是因为不同的克伦人都在重复它。割完稻子的聚餐上,我从他们热火朝天的讨论里了解到,整个水稻种植周期中,除了十到十一月收割,六月插秧和七月薅草他们也会互相帮忙,这意味着每年十二个月里,有将近四个月要一起合作,占了一年的三分之一。在原本的地缘和血缘连接之上,又形成另一层紧密的关系网。
一直以来我还很疑惑,村里几百个人,每天去哪儿帮忙的信息到底是如何通知到每家每户的?什么时间、哪些人去、如果同一天里有几家需要帮忙怎么办?除了年轻人,村民大多不用手机。这样组织几十个人的活动,他们根本不会提前约定,好像顺理成章地,大家都能抵达属于自己的位置。
每天像侦探般的观察也提高了我对细节的捕捉能力,感知也变得更敏锐。有天我起床很早,发现Kwiv的母亲在屋后的草地和一位五十岁上下的阿姨聊天,像是交换信息的样子。还有好几次我偶然出门,也在村子其他地方遇见她隔着篱笆和人说话。她有一个自己的圈子,或者说村里有无数个这样的圈子,交叉重叠,时隐时现。
另外在打谷时,大家各忙各的,看上去杂乱无章,其实也乱中有序。他们没有任何事先安排,没人告诉别人应该做什么,但无论男女老少,每个人都能在其中找到自己的位置,也从未出过差错。除了我。
阿姨和小姑娘们在田里拾稻,一怀一怀抱去田埂,青壮年们再把它卷做大捆扛到凉棚,阿姐和年长的阿叔在里头打谷,等所有稻谷都搬进凉棚,所有人又聚到一处。尾声通常是Kwiv的表兄弟戴着黑色面罩、背着长柄吹风机出现,这是整个过程中唯一使用机械的地方,用来吹除谷粒中的杂质。此时其他人就可以在木瓜树下喝水、休息了。不过还没结束,接着是装袋,所有妇女一哄而上,手拿铁盆,弓腰舀起谷子,迅速倒进干净的编织袋里。只有两三位年长的阿姨不同,她们胳膊下夹着细竹条,双眼巡视,四处走动,一旦看到哪个谷袋装满了,便冲上去抽出竹条,牢牢系住袋口。一旁的男孩子们也就知道,这时可以把它提上皮卡了。
事实上,这一切确实也都是不确定的,没有人有自己固定的“岗位”。只不过在这个还未完全受到工业化全面入侵的世界,他们对土地、传统和彼此的感知跟默契忠实地引领着他们。我所熟悉的工业体系下的那套管理、统筹、细节把控等等在这里完全失效。
在变化莫测的大自然中,他们灵活、自主、团结、富有体察之心,没有一个人是孤单的存在,大家彼此支持、依靠、信赖,才能拥有这样一个混沌而奇异和谐的系统。它表面上看不见摸不着,实则无处不在,某种程度上也映照着万物有灵的信仰,是这种信仰的物理体现。
印象最深刻的还有每次割谷到了最后,所有人不约而同来到同一块稻田,连成一排,挥舞着镰刀,就像一台怒吼的超大型联合收割机,甚至比它更令人仰视。
我放弃了询问“为什么不用机器”,意识到传统的协作关系丝毫不比机器逊色,甚至,它更加复杂、灵活、可持续、充满生命力。人不是机器的奴隶,而是土地上的国王。
不仅是返乡,而是选择农岛
一个月后,我跟着Kwiv打完大半农田,农岛的收割季也已接近尾声。他给自己放了一天假,带我去拜访村里返乡的克伦人。他们是老师、护士、建筑工、餐厅老板、有机农夫、旅游公司职员,也是诗人、音乐家和哲学家。当我问种植有机蔬菜的Triboon一年产量有多少时,他回答我从未算过,“光是种菜就很开心了,种了十年也不觉得累,和父母、妻儿在一起,好的空气、水和森林,有空就和家人到处旅行。”我们谈话时,他女儿正抓着菜棚的铁架当秋千荡着玩。
“为什么回家?”这是我向每个人提出的问题,他们都说:没有什么比留在家里更好的了。每次问,都是类似的答案。
最后,我也决定还是不问了,这确实是一个很傻的问题——我自己也觉得这里比哪里都好,只跟他们说:“I love this village,she makes me forget the past and don’t worry about the future,just live in the moment。”(我爱这个村庄,它让我忘记过去也不担心未来,只是活在当下)
农岛有一种魔力,让我内心平和、饱含力量。我可以信赖这里的每一个人;信赖日出、月圆、每年如期而至的春天;信赖一分耕耘一分收获;信赖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而不是金钱、房屋和保险。不管遭遇什么,我知道自己脚踩大地,和一群人一起生活。我也清楚地知道这里的一切也都在变化之中,但它的本质指向永恒。
放弃是一场漫长的排毒
最初来到这里的焦虑、失控最终在三周后彻底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一种越来越深刻的宁静的归属感。我愈来愈习惯听大家热闹开心地聊天,一起挥汗如雨,在累尽时有风从远方吹来,混合着干爽的泥土气息和金黄稻谷的味道,就像我们身体里也长着一片稻田。
回望这些日子,像是经历了一场漫长的排毒,我放弃了询问许多问题,放弃了追求计划跟可控性,从而获得自由、轻松、灵活、多变,可以像水一样融入克伦村的文化。
眼前是无处不在的阳光、风、花园、稻田和森林,可以随时随地奔跑、盯着一只鸟发呆、听它扑打翅膀、看它掠过深深浅浅、无数种绿色,消失在群山之后。我好像已经在这里生活了百年。
Kwiv的母亲每天会在天朦胧亮时起床,对面粮仓上的打米机总是准时响起,接着她会给鸡喂食儿,“咯咯,咯咯”“啾啾啾”“咯咯,咯咯” “啾啾啾”,高低错杂的叫声让人置身鸡的丛林。等我起床出来,火塘上闪着红光,锅里的米饭“咕咕”吐着气泡。Kwiv从外面进来,温棚里的菜苗浇过水了,果树四周的杂草也已打理干净,咖啡正一圈圈散着香气。“Keao,Keao”(我的泰语名字,意思是杯子。一开始我还抱怨这个名字普通,后来才发现,每当我发音不准时只要举起杯子,大家就都能明白我的名字,颇为好用),Kwiv的父亲拿出他的杯子,叫我去打杯咖啡。
我们沐浴在晨光里,盘腿坐在木板上吃饭,有时用勺子有时用手。布袋里放着Kwiv母亲用芭蕉叶包好的饭团,他父亲已经学会中文的“叔叔”、“阿姨”、“割谷”、“打谷”,并无师自通地告诉我今天“叔叔打谷”、“阿姨割谷”。我开始熟悉每个人的习惯,就如同他们开始接纳我成为家庭、村庄的一员。
离开前的一个夜晚,Kwiv问我在这里学到了什么?很多话都堵在喉咙,“kuangsu” (幸福),最后只有这个字蹦了出来。
每次劳作完,克伦人不会问我累不累,而是问我“享受吗?”他们认为对我来说这是工作,而劳作之于他们是生活,而且他们总是带着吃的喝的,开心享受着。前一天Kwiv的妹妹在劳作结束后问我“幸福吗?”我也是在那时学会这个新词的。
说完有点忐忑地看着他,等待即将来临的批评,可他嘴角上扬,仿佛正等这个答案:“如果你在这里感到幸福,一个月的学习就通过了。”
这是我们告别的话语,而我知道,我终将再次回到这个我信赖的村庄。
后记
我一直以为Kwiv对我在农岛的学习是没有计划的——他总是对我放任自由。直到研习结束后的分享会上,借由翻译,我才终于明白并不是这样,而他的计划就是没有计划。
他说:“在伍娇到来之前,我们就在思考,和我们返乡一样,到农岛虽然有多样的选择,但以农业为基础,再做其它发展更简单。农业最基础则是种稻子,所以她的学习也是从这里开始的。”
“伍娇来到这6个星期, 学习的不仅仅是知识,如果说只是学知识,农岛有一本厚厚的书,已说明了全部,但我更愿意她能够通过自去感知,参与到村庄活动,向社区学习,发现自己真正感兴趣的议题。”
“她经常问一些问题,村不是总能回答。有些问题并是一个答案可以解释的, 需要她自己去经历。不是一个月或者一就可以了解我们克伦族的全部。”
“我也告诉过她,我们有不同的文化,在这里学习之后要反身回去,学习自己的文化。”
中国-东南亚青年可持续生活研习计划
以推动青年参与生态农业和可持续生活为主要内容,特别关注传统智慧和文化传承、生态农业发展与绿色可持续社区建设的经验交流,积累青年参与社会发展的有效经验,增强各国青年的国际视野和实践能力。
伍娇
自由撰稿人。关注可持续农业与原住民文化,常年游走在山地部落,探寻古老的智慧与人性的光辉。微信公众号“兰那”(Landofric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