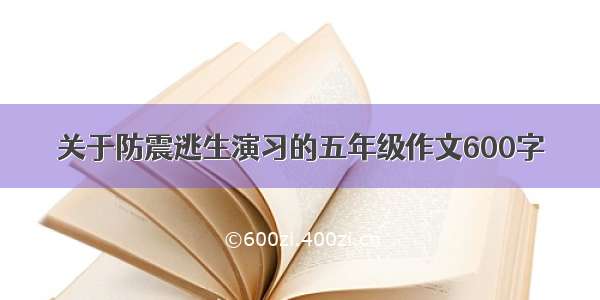大雪天细伢子玩得真韵味
∨
1954年,我刚进小学,正是天不怕,地不怕,疯玩的年代。我哥已是小学高年级,有他作后台,我每天屁颠屁颠的跟着后面玩得不亦乐乎。
寒假的一天早上,我还在赖床,哥哥突然把被窝一掀,几脚就把我从被窝里踢出来了哒。“快!快起来,玩雪去。”我们从床边的窗户中,看到外面白茫茫的一片。鹅毛大雪还在下个不停,窗户上的冰花,形态各异,煞是好看。
平时上学起床,我们总要母亲喊,搞得不好,还要用母亲绣花的托板一顿捶哒被窝,才慢慢吞吞、磨磨唧唧的起来。
纷纷扬扬的大雪下了一晚,积雪有脚背厚。早上起来,刚一开门,一股冷风夹着雪花劈头盖脸呛得我们喘不过气来。母亲在里屋感觉到了,把我们一顿臭骂:“两个死鬼,咯大的雪,出去窜死啊。你这个大家伙,不带好样啰。”哥哥赶紧把我往屋里一扯,把门只留一线缝:“冇出去呢,只在门口看看下雪。”雪下得太大了,风雪搅得天昏地暗,几米远都看不清,这个时候出去玩,那是找打,而且不好玩。母亲在里屋发话了:“把外面窗台上的冻豆腐拿进来,中午可以吃剁辣椒肉烧冻豆腐。”
“剁辣椒肉烧冻豆腐”,是母亲独创的私房菜。每当母亲知道要下雪了,就预先买回十几块豆腐,晚上用盆子把豆腐放在窗台上冰冻一晚,第二天就可以做菜了。冰冻好的豆腐,切开里面都是蜂窝状,烧剁辣椒或者烧肉,吃起来的那个香味,是嫰中有香,香中有嚼头。一口咬下去,剁辣椒和肉的鲜味就从豆腐蜂窝中渗透出来。那是越嚼越有味,越吃越想吃。几十年后的现在,用冰箱做冻豆腐,不管怎么样制作,就是不如天然的冻豆腐。
冻豆腐(图源网络,仅供参考)
下了一天两晚的大雪,今天早上总算停了。街上、屋檐上的积雪有一尺多厚,冰凌杆子都有一两尺长,走在雪地上咔嚓咔嚓响。关了两天的细伢子,如雨后春笋冒出来了。
我和哥哥跑向又一村草坪,突然,从四面八方飞来雪球,搞得我们一身雪花飞舞。“好哇!看我的。”我们预先做好了几十个雪球,用一个烂簸箕装了,哥哥把烂簸箕成半月形一挥,那几十个雪球如机关枪样哆……哆……哆,把那一群细份于搞得雪湖雪海。那个烂簸箕正好扣住光滴油的脑壳,把他的帽子也掀掉了。“啪!啪!”几个雪球打在光脑壳上,“哈!哈!”“喔呵……”“嘻嘻……啊耶,咯就眼法好啦。”打得光滴油抱着脑壳边笑边跑。
猫叽伢子拿来一条长板凳,把长板凳倒放在雪地上,就做雪橇玩。坐在上面找个下坡,用力一推,“喔唷!啊……”直个飚的溜下去好远。“嘿!咯比打雪仗好玩得多。”大家一窝蜂去找东西,长板凳、矮板凳、骨牌凳、竹椅子都我出来了。只看见那条街上,五花八门,乱七八糟的所谓之雪橇溜来溜去。“嘣!”光脑壳碰哒坨坨,猫叽伢子一下溜到沟里,差一点脑壳就碰到墙上。
“飃!驰……”猴子精坐在簸箕里呲的溜得好远,只看见他往旁边一歪,连人带簸箕从坎下张大爹的茅屋顶上飚过去,就像坐飞机样,一下就冇看见人哒。“崽啊崽,咯就不得了。”把我们看得目瞪口呆,“快跑!到张大爹屋前看看。”我们跑到张大爹门口一看,猴子精一个倒栽葱,正好跌得张大爹屋前的雪堆中。“哇塞!”“真过瘾”猴子精从雪堆里一飚就冲出来了。“哦!……”“啊!”大家兴高采烈地围着猴子精。
这年冬天是细伢子的玩雪天地。真爽!
手绘/萧山
学阉鸡,闯下大祸
∨
鸡鸭巷就是现在黄兴北路的燎原巷,西起藩城堤,东到一路吉祥。上世纪六十年代前,还一直叫鸡鸭巷。大约在1972年,在鸡鸭巷的东北建了燎原电影院,鸡鸭巷也就改成了燎原巷。
小时候,我们经常邀伴到鸡鸭巷看阉鸡。我们最喜欢看唐大爹阉鸡,到他这里来阉鸡的都要排队,他阉鸡的时候牌子十足,呷几口酒运半天神。
他把阉鸡的工具泡在一盘清水里面,手脚麻利的抓住公鸡,将鸡头一扭,把它包在鸡翼下。左脚踩哒翅膀,右脚踩住爪子,左手在鸡翅膀下边“刷刷刷”几下就拔光一片鸡毛。右手从盘中捞起一把一头像摄子般的阉鸡刀飞快地切开一条道子,再用一把两头带钩,俗称“铁弓”的工具,把那条“道”开肚后将铁弓锁定口子,接着用一根尺吧长、一头系着条细线儿,像枚缝衣针的铁丝,伸进口子里头,捻起线儿拉扯几下,便用一个小勺子把鸡肚子里的一点肉坨坨,从里面掏了出来,后来才知道是鸡的睾丸。掏完后,就掰开鸡的嘴巴灌上几滴水,一只鸡便阉好了。那鸡一松手就活蹦乱跳的,又冇出什么血,一点也不像动了手术,看得我们起鸡皮疙瘩,目瞪口呆地,但又兴致勃勃。
回来后,我们几个细伢子就学样,满院子抓鸡,搞得鸡飞狗跳的,好不容易抓了一只鸡我们用铅笔刀和铁丝就嘎场哒。抓的抓鸡脚,抓的抓鸡翅膀,抓的抓鸡脑壳。用铅笔刀在鸡肚子上一划,突然,鸡一顿乱窜,“叭!叭!”鸡屎、鸡毛沾了我们一身,卟……的一声,鸡一下就飞走了。“咯是哪个背时鬼啰,把我的鸡搞得四路子飞。”鸡的尖叫引来了满姨的一顿臭骂,“又是你们咯几个猫弹鬼跳的鬼崽子。”“快跑!快……快……”满姨左手拿揸扫把,右手拿叉子满院子追打。
这个祸闯得不小,当晚,我们这几个细伢子,不是撩刷丫子炒肉,就是跪搓衣板。
玩也玩了,骂也骂了,打也打了,我们的童年就是咯有味。
鸡鸭巷,你是否还记得我们这群细伢子来看过你的热闹?
*图源/陈先枢
楠木厅2号院的那群细牙子
∨
几十年前的楠木厅,多为深宅大院,虽然没有商铺老街那样热闹,但是跑来跑去的黄包车人力车倒是不少。街上的细伢子看到黄包车来哒,就偷偷地跟着跑,抓着车后面的车杠子一跳,就免费坐了一趟黄包车,好不韵味。等车夫看见,一鞭子抽过来时,这些细伢子笑哈哒的多时跑得没有影了。
楠木厅2号原是长沙公馆大宅院,坐北朝南,前庭后院,后院中有一口清澈的水井,四天井大堂屋,两层楼,东西厢房,大大小小有四十多间房。大门前有一对两米多高的石狮,大宅院是四米高的青砖围墙。
解放初私房改造,楠木厅2号大院子住了十几户居民,细伢子又多,一天到晚闹唔哒堆。一溜通的大堂屋,靠墙边尽是细伢子挖的玩弹弹的土坑。下雨天,堂屋里就是细伢子的天下,玩弹弹的,玩洋菩萨的,跳橡皮筋,滚铁环的,那闹喔!叫喔!热闹嗓哒。
这群细伢子里面,有个最调皮的得螺伢子,他就是平时得螺玩得好,抽得那得螺呼呼地转,他的得螺上用蜡笔涂得乱七八糟的。但是,一玩起来,那五颜六色的得螺转得人眼花缭乱,而且得螺伢子还可以从这只手转到那只手,逗得细伢子悦喊悦叫:“喔……哇塞!”“快抽,弹起来了。”“啪……啪……”“这几鞭子抽打得带劲来,越转越快,啊!”
天井里有两颗大桑树,每年春上到喂养蚕子的时候,细伢子的玩兴转了方向,好多细伢子用废洋火盒子(火柴盒)及其他的旧纸盒用来养蚕。到了下午放学后,细伢子分成两拨,几个细伢子缠哒看院子的王大爹,帮他扫地,捡树叶子,其他细伢子就偷偷爬上树,摘了桑叶往书包里放。王大爹对细伢子还是蛮好的,他就是怕细伢子把桑树叶一顿乱扯,莫把桑树搞坏了。不过,王大爹那根一米多长的烟袋杆,就蛮吓人,要是被他看见把桑树枝搞断了,那一烟袋脑壳敲下了,那脑壳上立马就会肿起一个鹅丁跟。
有次,星期天,得螺伢子上树摘桑树叶时,他几下几下就爬上去了,还有开始摘时,他突然在树上唧叫地:“快让开!我要屙屎了,快点!快点!我要忍不住哒。”在他下面还有两个细伢子,赶快往旁边爬。那个光脑壳还没有爬得赢,只听得“咚”的一响,一坨硬屎从得螺伢子裤脚里正好跌在光脑壳上,气得光脑壳又哭又叫,用桑树叶子使劲抹,那里晓得,越抹越臭,越抹越多。得螺伢子也顾不得那么多了,一看离地下还有2米来高,把书包一丢,就跳下来了,幸亏是泥巴地,打了两个滚,就往茅屎屋里跑。
得螺伢子晓得这次撞了大祸,屎屙得身上哒,还搞得光脑壳脑壳上哒。这不得了,回去有下饱的打。果不其然,得螺伢子中饭都冇得呷,被他娘老子用撩刷芽子(以前打细伢子的竹枝)追得满屋跑。从屋里追到屋外,追到堂屋时,等得螺伢子跑过去,这些细伢子就把板凳、扫把、簸箕拦在路上,这样一来,他娘老子就追不上得螺伢子哒。
得螺伢子一溜烟跑到菜园,突然鬼喊鬼叫:“你们快来看呀,胖胖在呷猪奶,胖胖在呷猪奶,啊耶!他还呷得蛮有味呢,快点喊胖姨来,她的崽在呷猪奶。”胖姨裤子还没有扎紧,就从茅屎屋里跑出来了:“啊耶!我的崽,我只去解一下手(上厕所)你就爬得咯里来哒,咯是哪个该死的,把我崽的站栏都搞倒哒。王大爹呢也是的,又把咯窝猪崽子放出来哒。”胖胖可不管他娘何什喊,白嫩哒的脸上沾满了猪奶,两只小胖手一边抓着猪奶头,叭嗒!叭嗒!正一个劲的吮吸着猪奶。
楠木厅深深地留下了我的童年趣味。
街区改造后新修缮供参观的露天楠木厅
糊衬壳子
∨
我们那条街上,每年一到六月伏天,差不多家家户户的门口都立一块门板。每块门板上都糊满哒乱七八糟的烂布巾,红的绿的黄的日的黑的麻的,什么颜色都有。那一排排的五花八门的装饰图案,简直是到了联合国的万国村,蔚为壮观。
如果放在现在,就是返璞归真的一道亮丽的、独特的民俗民情景观。
那一年,刚过头伏,一到晚上妈妈就把家里烂被单,补得不能再补的旧衣服全清理出来。我们那个年代的衣服,是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而且是老大穿不得就给老二,老二穿不得就给老三,就这样一个接一个,实在穿不得就拆了做衬壳子。每件衣服的扣子,妈妈都要拆下来,做以后的缝缝补补,那硬是冇得一点丢的。拆下来的旧布,小到一寸,大到几尺,就是大的旧床单、被单,也要撕扯成一二尺大,便于裱糊。
旧布都准备好了,第二天一黑早,妈妈就把这一天的饭都煮成撩米饭,留下米汤。吃过早饭,就把门板取下来。那时候的门板大部分都有门垛子,随时都可以取上取下。
糊衬壳子时,打底的第一块布有一二尺大,妈妈用鬃毛刷子把米汤刷在门板上再把布糊上,我们几姊妹就跟妈妈递布,“妈妈,用我这一块,几好看的,花楞哒的。”“妈妈,快用咯一块啰,通红的,糊得上面,就像太阳样。”我拿着自己原来穿的一件格子布,一顿乱舞哒,把妹妹掀开:“不,不,先糊我的咯块格子布哕。”一下冇搞得好,把米汤刷子搞得一飚,把米汤飚的妈妈和妹妹一身,我晓得这下拐哒场,把布一丢,就一溜烟的跑开哒。
衬壳子要糊得均匀,一块块的旧布一层层的糊上去,大概要糊十几层。糊好后,要放在大太阳下扎扎实实晒几天,干透好,就把门板上的衬壳子整块取下来。
到了秋冬,妈妈就会把我们全家大小的鞋帮子、鞋底在衬壳子上一块块剪好。不要好久,我们就有新布鞋穿了。这可是地地道道的凝聚着慈母心的手工布鞋。
纳布鞋(图源网络,供参考)
油桐油
∨
零售桐油,现在市面上,包括乡下,恐怕都是没有卖的了。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长沙好多日杂店的门口,多有用大木桶装的桐油零售,好像是0.28元一斤。桐油生意最好的时间是最热的大伏天。
记得那一年的八月,妈妈要哥哥去买几斤桐油,准备把屋里的吊桶、提桶、洗碗盆、脚盆都油上桐油。这些木盆、木桶,每两年就要油一次桐油,要不用不了几年,就会开裂漏水。不晓得何解,这一年桐油缺货,哥哥从中山路找到西长街、北正街、湘春路,转来转去,费了好大的劲,才在新河郊区日杂店买到了桐油。
妈妈要我们把屋里的这些吊桶、提桶、洗碗盆、脚盆,都拿到太阳下晒,要晒得交吧厉干都开裂了,才好油桐油。隔壁郑叔叔看到我们屋里晒提桶、脚盆,就晓得我们要油桐油了,热情地说:“满婶子,你屋里准备油桐油,那咯几天就到我屋里来拿吊桶提桶用啰。”“你如果不嫌弃,就用我屋里的脚盆噻。”对门王娭毑对我妈妈笑着说。王爹爹端了一杯茶,边走边喝:“你这个洗臭脚的哪用啰。”王娭毑也不示弱,笑着说:“你冇长眼睛,咯是洗脚盆啊,咯是洗澡的呢,我天天用开水烫过哒。你咯只老不死的。”这俩爹爹娱地,最喜欢斗杂嘴子。妈妈笑着说:“不嫌弃,不嫌弃,你屋里爱干净,那个不晓得啰,打锣都找不到了。
真怀念当年平房老院子,那个屋里有事,一声喔喝,左邻右舍帮忙的就都来了。
油桐油,大家不会一起搞。因为油一次桐油,至少要一个星期,搞得不好,还要十天半个月。相互错开,就是为了方便大家。
当那些木桶、盆都晒得差不多了,妈妈和哥哥就把揉成团的棉布,放在桐油里浸足油,然后就往木桶子、木盆子上死劲反复揉擦,要让这些木桶、木盆吸足桐油。当桐油油好后,就不能再放在太阳下晒了,只能挂起慢慢阴干。
我们家里的木水桶、脚盆,用了几十年,越用越油光发亮。
给木质家具刷桐油(图源网络,仅供参考)
母亲的绍兴腐乳
∨
1957年,父亲在河南郑州被打成右派,一家大小六口人的生活一下就陷入了困境。
因生活所迫,母亲和我们家亲戚也是邻居三伯妈,一起商量该做点什么。正好我家楼上胡娭毑的崽是做小菜生意的,每天拖一板车菜在街上叫卖。他出点子说:“现在街上绍兴猫乳(腐乳)好买,进一坛猫乳9块钱30斤,是30斤净猫乳。挑到外面卖,可以卖一分钱一片,一坛猫乳最少可以赚4-5块钱,运气好的话,几天就可以卖完。”
母亲一听,一坛可以赚这么多钱:“那连坛子一起有多重呢,何是挑嘞。”“那连坛子带猫乳只怕会有四五十斤,猫乳不能拆出来卖,要从坛子里就拿就卖才新鲜。如果想做,我还可以帮你们进一坛试一试。”三伯妈赶紧说:“那要得,我们两个人抬啰,只要有钱赚,管他的,试试看,吃点这样的苦,也算不了什么。”
第二天,胡娭毑的崽帮忙进了一坛绍兴腐乳,坛子是圆肚形,坛子外面还有藤条包装。母亲和三伯妈把猫乳坛子用绳子一兜,二个人一抬哒就开始游街叫卖。她们沿着潮宗街、寿星街、高升坪、马王塘、培元桥等十几条街转来转去。头次做这样的生意,游了半天的街巷,脚走痛了,肩膀压肿了,喉咙也喊干了,猫乳也没有卖出几片,而且还听点尽空话,“白白净净的细皮嫩肉,喊的什么啰,听都听不清,不像个做生意的。”
晚边子,母亲一进屋,我们看到母亲累得要死,五姊妹一下就长大了,打的打热水,拿的拿毛巾,搥的搥背。二个细老妹抱看母亲哭:“妈妈!妈妈!你明天莫去了。”随着伸出小手:“我有钱,把你。”“我有。”“我也有。”我们姊妹拿出了往年舍不得用的压岁钱,几分、几角,都是斩顿的新票子。母亲强忍着泪水笑着说:“快把压岁钱收起,冇事冇事!这一点苦算不了什么,头难头难。过几天就好了。”
经过几天的适应,母亲好多了,个多星期下来,腐乳也卖了一些。后来,母亲在腐乳坛子上面,用一个小碟子里面放二片腐乳,边走边吆喝:“一分钱一片的绍兴红猫乳,又辣又香又好吃,不信可以试味来。娭毑,试点味啵,蛮好吃的。”那时候,很多人吃饭,就是端了饭碗走东家窜西家,边走边吃。母亲这样做还蛮管用,只要有人试味开场买,那就是活广告,连锁反应,你买几片,他买几片,搞得好一下就可以销好几十片。
有次,经过单位食堂门口,母亲又搞起促销来,对食堂大师傅说:“一角钱10片,我送你一片,你买的越多我就送的越多。”那个大师傅一听,还有点油水捞。一口气就买了五十片,送他的五片,就带回自己家。
母亲的绍兴腐乳搞了几个月,也卖了上十坛子。那年,我们也过了一个略为热闹而又平淡的年。年三十晚上,母亲还是给我们没人一张二分斩顿的新票子压岁钱。END*节选自书籍《潮宗古街》,作者罗斯旦。编辑 | 明明。图源 | 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