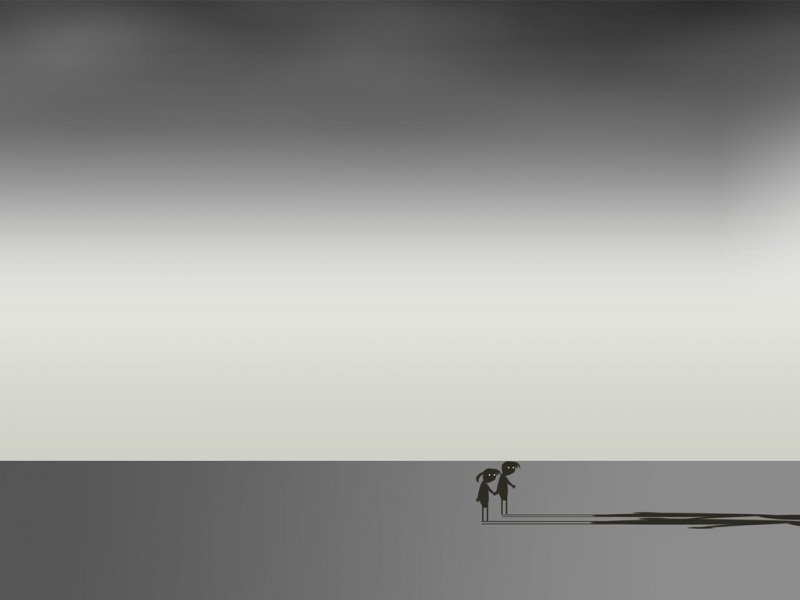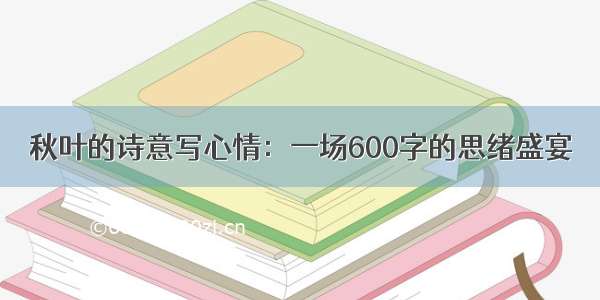杨赤大连京剧院院长,国家一级演员,袁派花脸。大连市戏剧家协会主席。梅花奖、梅兰芳金奖、白玉兰奖等多项大奖获得者。工架子花脸,兼工铜锤和武花脸,有“全才花脸”之誉。
近些年,他扛起传承和发展袁派艺术的大旗,为弘扬光大袁派艺术不遗余力,成为袁派艺术的领军人物和学术带头人。
他放弃了京津沪向他伸出的橄榄枝,甘愿带领一个萧条的剧团闯天下;他摘掉练功场上“面向全国,走向世界”的标语,让他的伙伴快乐工作,继而走向殷实生活。
燕升访谈:叱咤山海间
在当今京剧界,架子花脸难找,架子花脸能够做到铜锤唱,犹如凤毛麟角更难寻觅了。京剧界历来就有“千生百旦,一净难求”之说。
1982年,当时的大连京剧团为培养青年演员请来了京剧袁派创始人袁世海先生来大连授艺。年事已高的袁世海先生多年来一直寻觅高足,看到虎头虎脑的杨赤,袁世海不觉眼睛一亮:这个年轻人相貌酷似自己当年,嗓音宽亮厚重,文武基本功也扎实……一个正遍寻良师,一个正苦觅高徒,二人一拍即合。在大连市有关领导的安排下,一杯清茶,杨赤便正式拜袁世海先生为师。
如今,做为大连京剧院院长的杨赤已具有了架子花脸,铜锤花脸和武花脸的多重功力,也许是这个行当感染了他的性格,他很讲义气、重情义。
金秋十月,第五届中国京剧艺术节上,大连京剧院的新编历史剧《风雨杏黄旗》一炮打响荣获金奖,恢宏的场面,深邃的内涵,传神的刻画和淋漓酣畅的演唱,使圈内外赞叹不已。杨赤在《风雨杏黄旗》中为我们塑造了一个崭新的李逵。我想,有着“活李逵”美誉的袁世海先生九泉之下有知,一定会欣慰的。
白燕升:很长一段时间,杨赤一直跟国家京剧院合作,排了好多戏,以至于很多戏迷都觉得你就是北京的,可是这么多年来你一直在大连,杨赤的角色也一直在变换,由原来的大连京剧团团长,到现在的大连京剧院院长。大连固然是个好地方,这样一座不大的城市,会不会多多少少束缚了你?
杨赤:我常常跟朋友说,我是一个不太有出息的演员,为什么这么说呢,我考虑事情不像一些非常执着的艺术家那样,完全从艺术上考虑,艺术只是我其中很重要的一部分,还应包括其它更多方面。所以我觉得多多少少受一些影响。
白燕升:我听得出来,艺术不是杨赤的全部,杨赤还是一个注重生活质量生活品质的人,觉得在大连生活得非常得安逸和舒服?
杨赤:确实在大连的根扎得太深了,你走了似乎也觉得对不起大连这帮哥们弟兄,当时没有离开大连就是割舍不下对大连的这种情感。我在北京拿了梅花奖甚至在梅兰芳金奖获奖以后,包括中国京剧院,还有些领导希望我能到北京,那个时候确实心里有点动了。后来之所以没走成,其中一个主要的原因,那个时候,大连京剧院是非常困难的一个时期,如果我离开了大连,无形中给大连京剧团多少能带来一些困难,这个困难会直接影响到我这些同学们,都将近四十岁的人了,改行来不及了,退休又早点,不如留在这儿,大家一起把大连京剧院做好。不是说我杨赤有多么高的思想境界,我获得的所有的奖,梅花奖、梅兰芳金奖,包括文华奖,都是在大连京剧团获得的,这些奖的后面有大连市的家乡父老,大连市方方面面的领导,包括大连京剧院我这些同学们的支持帮助,人不管走到哪一步,怀着这样一颗感恩的心,肯定走得更踏实、也更明白。
白燕升:杨赤现在是院长,当初是团长,当领导有十年了,说说十年前,怎么想到要当这个团长?
杨赤:不是主动的,也不是有意识地想去当团长,当时就是想怎么把戏唱好,一心一意地就想跟着袁世海老师,把他的艺术怎么学好,其他的事儿想的不是很多。后来有一件事情对我的感触比较深刻,我记得中国京剧院的高文澜老师给我写了个剧本,叫《梁山恨》,当时我非常感动,把这个本子拿回团里,请孙元意老师给我们排这出戏。当时排练场的创作氛围总感觉不是太理想,团长在,大家的情绪就比较高,领导不在,大家的情绪就比较低沉,似乎不是为自己干事儿,是为领导干事儿。要知道,创作一出戏,需要大家一起来投入的。当时我非常苦恼,我跟谁,我跟他,跟乐队,我们平时都挺好的,都是从小一起长大的哥们,没什么矛盾,我排戏他怎么不认真?后来有人跟我说,杨赤,你不要想的太多,大家对你一点意见都没有,问题不在你杨赤身上,他跟你杨赤傍好了,跟你杨赤配合好了,与他分房子、涨工资,与他的一切一切没有关系。我觉得这个话说得有点偏颇,但还是有一定道理的,这是现实。那个时候我就想,将来有机会我也当团长,我当团长了再排戏。
白燕升:作为传统艺术,尤其作为戏曲,从古到今其实还是一个讲究角儿的艺术,是一个演员中心制的艺术。杨赤觉得一定要当团长,要有话语权,要把戏排好,这样能更好地调动大家的积极性。我很想知道,十年前接手了大连京剧团,那个时候的景象很风光吧?
杨赤:那个时候可以说用非常惨来形容。上面来宣布杨赤当团长,当时那五分钟,确实有一种挺荣光的感觉。没过十分钟回到团里,无数个问题出现在你面前,你一点感觉都没有了。举个例子,我当了团长,马上就过春节,我们办公室主任说,团长每年过春节之前必须得到老干部老师家去走访。我说好,你领着我走,今年就不按照级别了,我们按照哪位老先生岁数最大,第一到他
家。我记得团里有一个著名琴师迟德才老师,他九十多岁了,老先生看着我长大的。我说咱们先去看迟老师,一进门迟老师拿着一摞医药费,就是没报销的医药费说,杨赤,你当团长了我非常高兴,我是看着你长大的,我今年九十多了,你看我在临死之前能不能把我这点医药费给我报了?我不太愿意流泪,我当时几乎眼泪就下来了。从迟老师家出来,我说主任你走吧,我不能走了。因为我知道,到了第二位老前辈家里,仍然是医药费,因为当时大连京剧院有五六年没给老先生报医药费,每一位老前辈手里都攥着好几万的医药费。十年前那几万块钱,是一个非常大的负担。我说我没法儿走了,你代表我你走吧,我回来就想怎么能解决这个问题、后来我们统计完,有几十万的医药费,一块就给报了。后来我在剧团非常困难的情况下,坚持参加医疗保险,虽然每年拿出十几万,当时这十几万对我们团来说是一笔不小的开销了,我说一定要参加,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老的时候。
白燕升:当初自己当团长的初衷是想排戏,想有点话语权,可是没想到新官上任,首先面临的是这些老职工,老前辈的医药问题,和生活艰难的问题。咱们的排练场贴着一幅标语叫做“立足东北、面向全国、走向世界”,我听说你一上任,就把标语摘下去了?
杨赤:是。这个标语没有错,但与当时的大连京剧团很遥远,不切实际。我当团长之后最怕的日子就是每个月的10日。10日是团里开饷的日子,那么我们还在为每个月的饷钱奔波,怎么能走向世界?现在全团上下,我们只有两个字:“生存”。
白燕升:非常清醒。在物质非常匮乏,全团条件非常艰难的情况下,你给大家明确了一点,我们现在的主要任务是生存。你怎么给大家鼓劲?很多人估计还是看不到明天。
杨赤:没错!那个时候我就跟全团的同志们说,我们从事的是一项比较清贫的事业,如果说在座的要想追求金钱请改行,京剧恐怕一时半会儿不会给你这些东西。目前我们没有追求金钱的权利,但我们有追求快乐的权利,相互之间关系要融洽,一个单位,它的风气能改变一切。你这里要有好演员、好剧目,好的艺术水平。比如说有一些演员,虽然他在艺术上很有水平,他也是国家一级演员,也非常有影响,当他在剧团起到一种不太好的,或者是负面影响的时候,我宁肯舍弃你的艺术,我要保护剧团的一种氛围。我在努力改变大家经济状况的同时,在这方面也是我追求的一个目标。
白燕升:大连是座非常漂亮的美丽的花园城市,老百姓的生活也很殷实,也很富足,想当年,大连京剧团并不富裕,甚至用贫困来形容。尽管现在慢慢地好了,恐怕也没有跟上大连经济发展的步伐。但是无论有什么样的困难,我知道杨赤不管到北京,还是到全国其它地方演出办事儿,一演完出总是马不停蹄地要回大连,有一种归心似箭的归属感。
杨赤:是。从我学戏的那天起,一直到今天,时时刻刻在出现感动我的事情。我只说一件,我记得1993年,我进入了梅兰芳金奖决赛,我记得,进入决赛的几位演员,花脸演员全是京津沪。北京京剧院有黄彦忠,天津的是邓沐伟、孟广禄,还有康万生。还有上海的唐元才,加上我。当时竞争很激烈,因为那次打分挺有意思,现场评委是占百分之五十,那百分之五十是观众投票。这你知道,京剧的戏迷都有地域的感情色彩,并且大都集中在京津沪,大连的戏迷跟京津沪的戏迷从数量上那是没法儿比的。当时我非常担心,我说,这下可麻烦了,观众打分肯定没法儿跟京津沪去抗衡了。我就说了这么一句担心的话,旁边一位记者听见了,第二天我们《大连日报》的头版,这标题是什么呢?——“大连市民请投杨赤一票”。
白燕升:就是决赛当天?
杨赤:对,我当时非常非常感动,后来我问组委会,观众的票怎么样?对方说没问题。
白燕升:这件事儿让人感动。说到杨赤,不能不提到他的恩师,著名花脸表演艺术家袁世海先生,袁世海先生就海葬在大连?
杨赤:是。
白燕升:有什么特别的用意吗?
杨赤:老师跟师娘都属大龙的,他说我们都商量好了,将来就是海葬,不给后代留麻烦。我不但艺术上佩服我老师,在这方面我也非常敬佩他,他之所以选择在大连海葬,用他的话说,杨赤,将来我海葬在大连,我要看着你怎么样把架子花脸发展下去,这是一种情怀。我师娘早先生五年去世的,海葬的时候,老师也跟着一块出海,把师娘骨灰撒到大海的时候,老师还跟我说,将来你得给我记住了这地儿,将来也得给我放在这儿。当时确实感受到了艺术大师的一种胸怀。
可能大家不相信,我从拜老师到他去世二十年,我没给老师一分钱,老师没收过杨赤一分钱。我记得1982年拜完师之后就是演出,他带着我演三场《九江口》,《九江口》那戏是非常累的,演了三场《九江口》最后盈利一万块钱。当时领导认为这个钱理所应当是归袁世海老师,当把这个钱拿给袁世海老师的时候,老师说这个钱我不能要,这个钱留着给杨赤制几身蟒。我看他那个蟒太陈旧了,这就是我所知道的,真正的袁世海。
白燕升:跟袁老师学了二十年,我听说前十年几乎没怎么学,就是照顾老师的生活,好好跟老师相处,希望在生活当中有一种默契,后十年才正儿八经地跟他学,是这样吗?
杨赤:非常准确。一开始我对老师更多的是一种仰望。袁世海艺术大师到了大连,作为一个学生最主导的思想让老师高兴,让老师吃好、住好,生活得愉快,学戏不是想的太多,这是前十年。后来随着年龄的增长,对艺术的认识,特别是老师反反复复的教育,逐渐开窍了,对老师的艺术才有一种真正的理解,有了真正的理解就有了真正的崇拜。以前的崇拜是空的,就知道好,好在哪儿不知道,现在我明白老师好在什么地方,就想学了。后十年跟老师学的东西比前十年要系统,要多得多。我记得袁世海老师有一句话,他反复地说,你一定要记住,我们的架子花脸是“高级味精”。“高级味精”就是说架子花脸不是主菜,我们更多的是要起到一种调味的作用,不像老生旦角那样,经常地站在舞台中间,但是这不等同于降低艺术水平。我觉得袁世海老师用他自己的实践说明,艺术绝对不是用数量和时间来衡量的,这是一个架子花脸要追求的,也是我追求的一个目标。
白燕升:从杨赤,到他的老师袁世海先生,再到袁世海先生的老师郝寿臣先生,一脉相承追根溯源,我仿佛看到了前辈艺术大家塑造的一系列人物,后来的人们总习惯在这些人物前面加一个“活”字,活曹操、活李逵、活鲁智深、活张飞、活李七……把人物塑造“活”是需要手段的,那就是既要有嗓子,又要有膀子,更要有真情实感,为人物而唱,为人物而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