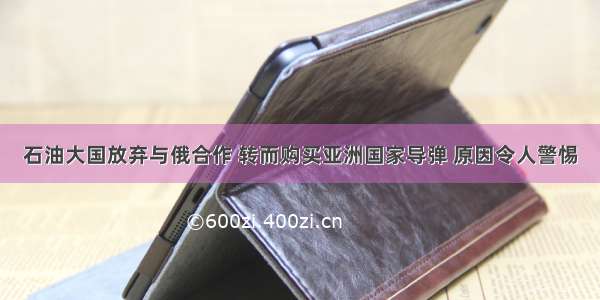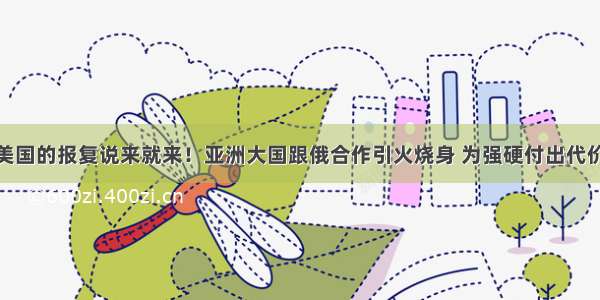在阅读文章之前,您可以先点击上方的蓝色字体“清风绕指柔”,再点击关 注,这样您就可以每天都可以收到小编为您精心准备的文章了,完全是“免费订阅”,请放心关注。
亚洲大国刚恢复对华出口,又双叒叕毁约,中:还好早有准备!都知道“怀璧其罪”的道理,而这道理也适用于每一个国家,有丰富资源对一国来说其实是一把双刃剑,若是拥有稀缺资源的是没实力的国家,那么恐怕会引人哄抢,比如非洲坦桑尼亚在8月10日发生的油罐爆炸事件,8月21日时该地区的国民医院才在采访中透露死亡人数已经上升到100人,非洲也有很丰富的石油资源但却没有开采、提炼技术,在油罐车翻车之后,附近的居民不知道其隐患就开始哄抢,从5月初到8月底,非洲起码发生了不下十次的爆炸案。
石油作为一种不可再生的资源,其价值对一个贫油国来说非常重要,不然一开始美国对伊朗下达石油出口禁令时,印度不会变得那么紧张,同样的伊朗作为石油大国也成为了美国要对付的目标,经济制裁、军队威慑、窃取情报等手段层出不穷,几个月以来伊朗民众因美国的极限施压而弥漫着灰色气氛,凡是利用价值很高的资源总会有人竞相购买。
而我方也有稀缺的矿产资源,为了保护稀土,我方已经对西方下达了禁令,让特朗普着急地四处寻找稳定的供应商,尽管美国有着丰富的天然气资源,但稀土却被人卡脖子,同样地我方虽然也有稀土,但所需要的镍矿也非常庞大,作为泱泱大国很多中老年人都患了糖尿病,这就致使医院需要很多胰岛素,而镍矿资源能激活胰岛素,在医用领域价值极高。
假如这时候窗子外有雪——街上,城墙上,屋脊上,都是雪,胡同口一家屋檐下偎着一个戴黑兜帽的巡警,半拢着睡眼,看棉团似的雪花在半空中跳着玩……假如这夜是一个深极了的啊,不是壁上挂钟的时针指示给我们看的深夜,这深就比是一个山洞的深,一个往下钻螺旋形的山洞的深…… 假如我能有这样一个深夜,它那无底的阴森捻起我遍体的毫管;再能有窗子外不住往下筛的雪,筛淡了远近间飏动的市谣;筛泯了在泥道上挣扎的车轮;筛灭了脑壳中不妥协的潜流…… 我要那深,我要那静。那在树荫浓密处躲着的夜鹰,轻易不敢在天光还在照亮时出来睁眼。思想:它也得等。 青天里有一点子黑的。正冲着太阳耀眼,望不真,你把手遮着眼,对着那两株树缝里瞧,黑的,有榧子来大,不,有桃子来大——嘿,又移着往西了!一夜之间,一场雷电引发的山火烧毁了美丽的“森林庄园”,刚刚从祖父那里继承了这座庄园的保罗·迪克陷入了一筹莫展的境地。他经受不起打击,闭门不出,茶饭不思,眼睛熬出了血丝。一个多月过去了,年已古稀的外祖母获悉此事,意味深长地对保罗说:“小伙子,庄园成了废墟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你的眼睛失去了光泽,一天一天地老去。一双老去的眼睛,怎么能看得见希望?”保罗在外祖母的劝说下,一个人走出了庄园。他漫无目的地闲逛,在一条街道的拐弯处,他看到一家店铺的门前人头攒动,原来是一些家庭主妇正在排队购买木炭。那一块块躺在纸箱里的木炭忽然让保罗的眼睛一亮,使他看到了一线希望。于是在接下来的两个星期里,保罗雇了几名烧炭工,将庄园里烧焦的树木加工成优质的木炭,送到集市上的木炭经销店。腊月回乡祭祖,在老家逗留了几日,临别出山那天,堂弟送了我一盒年糕。所谓年糕,其寓意乃年年高的意思。按习俗,年糕是过年必备食物,平日鲜见,只有临近春节,才有它的身影。孩提时代,我最喜爱过年,每逢辞旧迎新之时,除了点炮竹,换新符、穿新衣外。还有一道难忘的口福,便是品尝母亲亲手蒸制的年糕,嚼起来甜滋滋,软绵绵,圆润鲜美,馋涎不止。说实话,母亲心灵手巧,是制作年糕的一把好手,每逢到了腊月廿四,母亲便着手这项工作,从备料到加工,都作了精细准备。记得每年秋后,母亲就托人从老家捎回一些粳米,这些米属单季稻,由于生长周期长,质软粘性好,是制糕的上等原料,如果再配加一些上好的糯米,做出来的年糕,口感香软爽滑。想当年,制做年糕全凭手工操作,即便磨粉这样重体力的活,也要靠最原始的石盘磨碾,一人推磨,一人往石盘上面的圆孔里撮撒米料,干起来即费时又费力,所以这些事,平常都属于男人干的,而我家例外,由于父亲长年被流放在外,只能由母亲独担。现在回忆起来,很难想象当年的母亲,以她那瘦弱之躯去完成这样一件工作。母亲推碾磨粉,力小速缓,有时不得已靠两手轮换使力,右手累了换左手,左手累了换右手,虽说磨盘转速缓慢,却未停歇。站在一旁的我,总要伸出助力的小手,拼力帮母亲推一把,希望替母亲省些气力。当一抹抹被碾碎的粉末,从磨盘的缝隙细细渗出,悄然地散落到沟槽中。看着那些粉未慢慢积堆起来,母亲的汗水顺着脸颊一直不断地滴落在地上。那暗淡的灯光,照着她满身疲累的背影……磨完粉,母亲将粉料放置大盆里,注入红糖水,调搅成稠糊状,用大木勺舀出,平摊入蒸笼内,中间还嵌放一些猪肉条或脱核红枣。加工年糕的蒸笼是竹制的,有三四层高,层与层之间用竹管连通蒸汽。蒸制年糕很费时,用木柴烧制,须花七八个小时。烧制一般从下午至午夜凌晨结束,这是一段最惬意的时间,吃罢晚饭,我偎依在母亲旁边,靠着灶堂口,借着柴火透出余温烤暖,一边听着母亲讲故事,一边看着干柴燃烧迸发的啪啪火星,心里盼着年糕早点出笼解馋,到了午夜时分,我瞌睡上来偎在母亲怀里睡着了,但心里总还惦记着年糕,时而会醒来问母亲,熟了吗?母亲垂头看着我说,快了!看着母亲那机械地往灶膛添柴的小手和满脸的倦容,少年的我,总觉得母亲太累……凌晨时分,母亲叫醒我,切下第一块年糕让我尝鲜,此时的我,跃雀,满足,幸福……几十年的时光一晃而过,藏在心底的那抹童真,那块年糕,成了我追忆母亲的情丝,萦绕于怀,每年回乡祭奠母亲,我总会带着年糕去……结果,木炭被抢购一空,他因此得到一笔不菲的收入。然后他用这笔收入购买了一大批新树苗,于是一个新的庄园初具规模了。几年以后,“森林庄园”再度绿意盎然。请记住:别让眼睛老去,才不会让心灵荒芜。眼睛如果老去,就无法看到希望,没有希望的人生,终将失去存在的意义。积极乐观地生活,忘掉悲伤与不幸,你一定会拥有无限的快乐。当你沉湎于曾经的悲痛时,也将失去今日的欢愉。挫折和痛苦来临之时,也许正是通往成功的开始。 我们吃了中饭出来到海边去。(这是英国康槐尔极南的一角,三面是大西洋)。勖丽丽的叫响从我们的脚底下匀匀的往上颤,齐着腰,到了肩高,过了头顶,高入了云,高出了云。啊!你能不能把一种急震的乐音想象成一阵光明的细雨,从蓝天里冲着这平铺着青绿的地面不住的下?不,那雨点都是跳舞的小脚,安琪儿的。云雀们也吃过了饭,离开了它们卑微的地巢飞往高处做工去。上帝给它们的工作,替上帝做的工作。瞧着,这儿一只,那边又起了两!一起就冲着天顶飞,小翅膀活动的多快活,圆圆的,不踌躇的飞,——它们就认识青天。一起就开口唱,小嗓子活动的多快活,一颗颗小精圆珠子直往外唾,亮亮的唾,脆脆的唾,——它们赞美的是青天。瞧着,这飞得多高,有豆子大,有芝麻大,黑刺刺的一屑,直顶着无底的天顶细细的摇,——这全看不见了,影子都没了!但这光明的细雨还是不住的下着…… 飞。“其翼若垂天之云……背负苍天,而莫之夭阏者;”那不容易见着。假如这时候窗子外有雪——街上,城墙上,屋脊上,都是雪,胡同口一家屋檐下偎着一个戴黑兜帽的巡警,半拢着睡眼,看棉团似的雪花在半空中跳着玩……假如这夜是一个深极了的啊,不是壁上挂钟的时针指示给我们看的深夜,这深就比是一个山洞的深,一个往下钻螺旋形的山洞的深…… 假如我能有这样一个深夜,它那无底的阴森捻起我遍体的毫管;再能有窗子外不住往下筛的雪,筛淡了远近间飏动的市谣;筛泯了在泥道上挣扎的车轮;筛灭了脑壳中不妥协的潜流…… 我要那深,我要那静。那在树荫浓密处躲着的夜鹰,轻易不敢在天光还在照亮时出来睁眼。思想:它也得等。 青天里有一点子黑的。正冲着太阳耀眼,望不真,你把手遮着眼,对着那两株树缝里瞧,黑的,有榧子来大,不,有桃子来大——嘿,又移着往西了!一夜之间,一场雷电引发的山火烧毁了美丽的“森林庄园”,刚刚从祖父那里继承了这座庄园的保罗·迪克陷入了一筹莫展的境地。他经受不起打击,闭门不出,茶饭不思,眼睛熬出了血丝。一个多月过去了,年已古稀的外祖母获悉此事,意味深长地对保罗说:“小伙子,庄园成了废墟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你的眼睛失去了光泽,一天一天地老去。一双老去的眼睛,怎么能看得见希望?”保罗在外祖母的劝说下,一个人走出了庄园。他漫无目的地闲逛,在一条街道的拐弯处,他看到一家店铺的门前人头攒动,原来是一些家庭主妇正在排队购买木炭。那一块块躺在纸箱里的木炭忽然让保罗的眼睛一亮,使他看到了一线希望。于是在接下来的两个星期里,保罗雇了几名烧炭工,将庄园里烧焦的树木加工成优质的木炭,送到集市上的木炭经销店。腊月回乡祭祖,在老家逗留了几日,临别出山那天,堂弟送了我一盒年糕。所谓年糕,其寓意乃年年高的意思。按习俗,年糕是过年必备食物,平日鲜见,只有临近春节,才有它的身影。孩提时代,我最喜爱过年,每逢辞旧迎新之时,除了点炮竹,换新符、穿新衣外。还有一道难忘的口福,便是品尝母亲亲手蒸制的年糕,嚼起来甜滋滋,软绵绵,圆润鲜美,馋涎不止。说实话,母亲心灵手巧,是制作年糕的一把好手,每逢到了腊月廿四,母亲便着手这项工作,从备料到加工,都作了精细准备。记得每年秋后,母亲就托人从老家捎回一些粳米,这些米属单季稻,由于生长周期长,质软粘性好,是制糕的上等原料,如果再配加一些上好的糯米,做出来的年糕,口感香软爽滑。想当年,制做年糕全凭手工操作,即便磨粉这样重体力的活,也要靠最原始的石盘磨碾,一人推磨,一人往石盘上面的圆孔里撮撒米料,干起来即费时又费力,所以这些事,平常都属于男人干的,而我家例外,由于父亲长年被流放在外,只能由母亲独担。现在回忆起来,很难想象当年的母亲,以她那瘦弱之躯去完成这样一件工作。母亲推碾磨粉,力小速缓,有时不得已靠两手轮换使力,右手累了换左手,左手累了换右手,虽说磨盘转速缓慢,却未停歇。站在一旁的我,总要伸出助力的小手,拼力帮母亲推一把,希望替母亲省些气力。当一抹抹被碾碎的粉末,从磨盘的缝隙细细渗出,悄然地散落到沟槽中。看着那些粉未慢慢积堆起来,母亲的汗水顺着脸颊一直不断地滴落在地上。那暗淡的灯光,照着她满身疲累的背影……磨完粉,母亲将粉料放置大盆里,注入红糖水,调搅成稠糊状,用大木勺舀出,平摊入蒸笼内,中间还嵌放一些猪肉条或脱核红枣。加工年糕的蒸笼是竹制的,有三四层高,层与层之间用竹管连通蒸汽。蒸制年糕很费时,用木柴烧制,须花七八个小时。烧制一般从下午至午夜凌晨结束,这是一段最惬意的时间,吃罢晚饭,我偎依在母亲旁边,靠着灶堂口,借着柴火透出余温烤暖,一边听着母亲讲故事,一边看着干柴燃烧迸发的啪啪火星,心里盼着年糕早点出笼解馋,到了午夜时分,我瞌睡上来偎在母亲怀里睡着了,但心里总还惦记着年糕,时而会醒来问母亲,熟了吗?母亲垂头看着我说,快了!看着母亲那机械地往灶膛添柴的小手和满脸的倦容,少年的我,总觉得母亲太累……凌晨时分,母亲叫醒我,切下第一块年糕让我尝鲜,此时的我,跃雀,满足,幸福……几十年的时光一晃而过,藏在心底的那抹童真,那块年糕,成了我追忆母亲的情丝,萦绕于怀,每年回乡祭奠母亲,我总会带着年糕去……结果,木炭被抢购一空,他因此得到一笔不菲的收入。然后他用这笔收入购买了一大批新树苗,于是一个新的庄园初具规模了。几年以后,“森林庄园”再度绿意盎然。请记住:别让眼睛老去,才不会让心灵荒芜。眼睛如果老去,就无法看到希望,没有希望的人生,终将失去存在的意义。积极乐观地生活,忘掉悲伤与不幸,你一定会拥有无限的快乐。当你沉湎于曾经的悲痛时,也将失去今日的欢愉。挫折和痛苦来临之时,也许正是通往成功的开始。 我们吃了中饭出来到海边去。(这是英国康槐尔极南的一角,三面是大西洋)。勖丽丽的叫响从我们的脚底下匀匀的往上颤,齐着腰,到了肩高,过了头顶,高入了云,高出了云。啊!你能不能把一种急震的乐音想象成一阵光明的细雨,从蓝天里冲着这平铺着青绿的地面不住的下?不,那雨点都是跳舞的小脚,安琪儿的。云雀们也吃过了饭,离开了它们卑微的地巢飞往高处做工去。上帝给它们的工作,替上帝做的工作。瞧着,这儿一只,那边又起了两!一起就冲着天顶飞,小翅膀活动的多快活,圆圆的,不踌躇的飞,——它们就认识青天。一起就开口唱,小嗓子活动的多快活,一颗颗小精圆珠子直往外唾,亮亮的唾,脆脆的唾,——它们赞美的是青天。瞧着,这飞得多高,有豆子大,有芝麻大,黑刺刺的一屑,直顶着无底的天顶细细的摇,——这全看不见了,影子都没了!但这光明的细雨还是不住的下着…… 飞。“其翼若垂天之云……背负苍天,而莫之夭阏者;”那不容易见着。假如这时候窗子外有雪——街上,城墙上,屋脊上,都是雪,胡同口一家屋檐下偎着一个戴黑兜帽的巡警,半拢着睡眼,看棉团似的雪花在半空中跳着玩……假如这夜是一个深极了的啊,不是壁上挂钟的时针指示给我们看的深夜,这深就比是一个山洞的深,一个往下钻螺旋形的山洞的深…… 假如我能有这样一个深夜,它那无底的阴森捻起我遍体的毫管;再能有窗子外不住往下筛的雪,筛淡了远近间飏动的市谣;筛泯了在泥道上挣扎的车轮;筛灭了脑壳中不妥协的潜流…… 我要那深,我要那静。那在树荫浓密处躲着的夜鹰,轻易不敢在天光还在照亮时出来睁眼。思想:它也得等。 青天里有一点子黑的。正冲着太阳耀眼,望不真,你把手遮着眼,对着那两株树缝里瞧,黑的,有榧子来大,不,有桃子来大——嘿,又移着往西了!一夜之间,一场雷电引发的山火烧毁了美丽的“森林庄园”,刚刚从祖父那里继承了这座庄园的保罗·迪克陷入了一筹莫展的境地。他经受不起打击,闭门不出,茶饭不思,眼睛熬出了血丝。一个多月过去了,年已古稀的外祖母获悉此事,意味深长地对保罗说:“小伙子,庄园成了废墟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你的眼睛失去了光泽,一天一天地老去。一双老去的眼睛,怎么能看得见希望?”保罗在外祖母的劝说下,一个人走出了庄园。他漫无目的地闲逛,在一条街道的拐弯处,他看到一家店铺的门前人头攒动,原来是一些家庭主妇正在排队购买木炭。那一块块躺在纸箱里的木炭忽然让保罗的眼睛一亮,使他看到了一线希望。于是在接下来的两个星期里,保罗雇了几名烧炭工,将庄园里烧焦的树木加工成优质的木炭,送到集市上的木炭经销店。腊月回乡祭祖,在老家逗留了几日,临别出山那天,堂弟送了我一盒年糕。所谓年糕,其寓意乃年年高的意思。按习俗,年糕是过年必备食物,平日鲜见,只有临近春节,才有它的身影。孩提时代,我最喜爱过年,每逢辞旧迎新之时,除了点炮竹,换新符、穿新衣外。还有一道难忘的口福,便是品尝母亲亲手蒸制的年糕,嚼起来甜滋滋,软绵绵,圆润鲜美,馋涎不止。说实话,母亲心灵手巧,是制作年糕的一把好手,每逢到了腊月廿四,母亲便着手这项工作,从备料到加工,都作了精细准备。记得每年秋后,母亲就托人从老家捎回一些粳米,这些米属单季稻,由于生长周期长,质软粘性好,是制糕的上等原料,如果再配加一些上好的糯米,做出来的年糕,口感香软爽滑。想当年,制做年糕全凭手工操作,即便磨粉这样重体力的活,也要靠最原始的石盘磨碾,一人推磨,一人往石盘上面的圆孔里撮撒米料,干起来即费时又费力,所以这些事,平常都属于男人干的,而我家例外,由于父亲长年被流放在外,只能由母亲独担。现在回忆起来,很难想象当年的母亲,以她那瘦弱之躯去完成这样一件工作。母亲推碾磨粉,力小速缓,有时不得已靠两手轮换使力,右手累了换左手,左手累了换右手,虽说磨盘转速缓慢,却未停歇。站在一旁的我,总要伸出助力的小手,拼力帮母亲推一把,希望替母亲省些气力。当一抹抹被碾碎的粉末,从磨盘的缝隙细细渗出,悄然地散落到沟槽中。看着那些粉未慢慢积堆起来,母亲的汗水顺着脸颊一直不断地滴落在地上。那暗淡的灯光,照着她满身疲累的背影……磨完粉,母亲将粉料放置大盆里,注入红糖水,调搅成稠糊状,用大木勺舀出,平摊入蒸笼内,中间还嵌放一些猪肉条或脱核红枣。加工年糕的蒸笼是竹制的,有三四层高,层与层之间用竹管连通蒸汽。蒸制年糕很费时,用木柴烧制,须花七八个小时。烧制一般从下午至午夜凌晨结束,这是一段最惬意的时间,吃罢晚饭,我偎依在母亲旁边,靠着灶堂口,借着柴火透出余温烤暖,一边听着母亲讲故事,一边看着干柴燃烧迸发的啪啪火星,心里盼着年糕早点出笼解馋,到了午夜时分,我瞌睡上来偎在母亲怀里睡着了,但心里总还惦记着年糕,时而会醒来问母亲,熟了吗?母亲垂头看着我说,快了!看着母亲那机械地往灶膛添柴的小手和满脸的倦容,少年的我,总觉得母亲太累……凌晨时分,母亲叫醒我,切下第一块年糕让我尝鲜,此时的我,跃雀,满足,幸福……几十年的时光一晃而过,藏在心底的那抹童真,那块年糕,成了我追忆母亲的情丝,萦绕于怀,每年回乡祭奠母亲,我总会带着年糕去……结果,木炭被抢购一空,他因此得到一笔不菲的收入。然后他用这笔收入购买了一大批新树苗,于是一个新的庄园初具规模了。几年以后,“森林庄园”再度绿意盎然。请记住:别让眼睛老去,才不会让心灵荒芜。眼睛如果老去,就无法看到希望,没有希望的人生,终将失去存在的意义。积极乐观地生活,忘掉悲伤与不幸,你一定会拥有无限的快乐。当你沉湎于曾经的悲痛时,也将失去今日的欢愉。挫折和痛苦来临之时,也许正是通往成功的开始。 我们吃了中饭出来到海边去。(这是英国康槐尔极南的一角,三面是大西洋)。勖丽丽的叫响从我们的脚底下匀匀的往上颤,齐着腰,到了肩高,过了头顶,高入了云,高出了云。啊!你能不能把一种急震的乐音想象成一阵光明的细雨,从蓝天里冲着这平铺着青绿的地面不住的下?不,那雨点都是跳舞的小脚,安琪儿的。云雀们也吃过了饭,离开了它们卑微的地巢飞往高处做工去。上帝给它们的工作,替上帝做的工作。瞧着,这儿一只,那边又起了两!一起就冲着天顶飞,小翅膀活动的多快活,圆圆的,不踌躇的飞,——它们就认识青天。一起就开口唱,小嗓子活动的多快活,一颗颗小精圆珠子直往外唾,亮亮的唾,脆脆的唾,——它们赞美的是青天。瞧着,这飞得多高,有豆子大,有芝麻大,黑刺刺的一屑,直顶着无底的天顶细细的摇,——这全看不见了,影子都没了!但这光明的细雨还是不住的下着…… 飞。“其翼若垂天之云……背负苍天,而莫之夭阏者;”那不容易见着。假如这时候窗子外有雪——街上,城墙上,屋脊上,都是雪,胡同口一家屋檐下偎着一个戴黑兜帽的巡警,半拢着睡眼,看棉团似的雪花在半空中跳着玩……假如这夜是一个深极了的啊,不是壁上挂钟的时针指示给我们看的深夜,这深就比是一个山洞的深,一个往下钻螺旋形的山洞的深…… 假如我能有这样一个深夜,它那无底的阴森捻起我遍体的毫管;再能有窗子外不住往下筛的雪,筛淡了远近间飏动的市谣;筛泯了在泥道上挣扎的车轮;筛灭了脑壳中不妥协的潜流…… 我要那深,我要那静。那在树荫浓密处躲着的夜鹰,轻易不敢在天光还在照亮时出来睁眼。思想:它也得等。 青天里有一点子黑的。正冲着太阳耀眼,望不真,你把手遮着眼,对着那两株树缝里瞧,黑的,有榧子来大,不,有桃子来大——嘿,又移着往西了!一夜之间,一场雷电引发的山火烧毁了美丽的“森林庄园”,刚刚从祖父那里继承了这座庄园的保罗·迪克陷入了一筹莫展的境地。他经受不起打击,闭门不出,茶饭不思,眼睛熬出了血丝。一个多月过去了,年已古稀的外祖母获悉此事,意味深长地对保罗说:“小伙子,庄园成了废墟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你的眼睛失去了光泽,一天一天地老去。一双老去的眼睛,怎么能看得见希望?”保罗在外祖母的劝说下,一个人走出了庄园。他漫无目的地闲逛,在一条街道的拐弯处,他看到一家店铺的门前人头攒动,原来是一些家庭主妇正在排队购买木炭。那一块块躺在纸箱里的木炭忽然让保罗的眼睛一亮,使他看到了一线希望。于是在接下来的两个星期里,保罗雇了几名烧炭工,将庄园里烧焦的树木加工成优质的木炭,送到集市上的木炭经销店。腊月回乡祭祖,在老家逗留了几日,临别出山那天,堂弟送了我一盒年糕。所谓年糕,其寓意乃年年高的意思。按习俗,年糕是过年必备食物,平日鲜见,只有临近春节,才有它的身影。孩提时代,我最喜爱过年,每逢辞旧迎新之时,除了点炮竹,换新符、穿新衣外。还有一道难忘的口福,便是品尝母亲亲手蒸制的年糕,嚼起来甜滋滋,软绵绵,圆润鲜美,馋涎不止。说实话,母亲心灵手巧,是制作年糕的一把好手,每逢到了腊月廿四,母亲便着手这项工作,从备料到加工,都作了精细准备。记得每年秋后,母亲就托人从老家捎回一些粳米,这些米属单季稻,由于生长周期长,质软粘性好,是制糕的上等原料,如果再配加一些上好的糯米,做出来的年糕,口感香软爽滑。想当年,制做年糕全凭手工操作,即便磨粉这样重体力的活,也要靠最原始的石盘磨碾,一人推磨,一人往石盘上面的圆孔里撮撒米料,干起来即费时又费力,所以这些事,平常都属于男人干的,而我家例外,由于父亲长年被流放在外,只能由母亲独担。现在回忆起来,很难想象当年的母亲,以她那瘦弱之躯去完成这样一件工作。母亲推碾磨粉,力小速缓,有时不得已靠两手轮换使力,右手累了换左手,左手累了换右手,虽说磨盘转速缓慢,却未停歇。站在一旁的我,总要伸出助力的小手,拼力帮母亲推一把,希望替母亲省些气力。当一抹抹被碾碎的粉末,从磨盘的缝隙细细渗出,悄然地散落到沟槽中。看着那些粉未慢慢积堆起来,母亲的汗水顺着脸颊一直不断地滴落在地上。那暗淡的灯光,照着她满身疲累的背影……磨完粉,母亲将粉料放置大盆里,注入红糖水,调搅成稠糊状,用大木勺舀出,平摊入蒸笼内,中间还嵌放一些猪肉条或脱核红枣。加工年糕的蒸笼是竹制的,有三四层高,层与层之间用竹管连通蒸汽。蒸制年糕很费时,用木柴烧制,须花七八个小时。烧制一般从下午至午夜凌晨结束,这是一段最惬意的时间,吃罢晚饭,我偎依在母亲旁边,靠着灶堂口,借着柴火透出余温烤暖,一边听着母亲讲故事,一边看着干柴燃烧迸发的啪啪火星,心里盼着年糕早点出笼解馋,到了午夜时分,我瞌睡上来偎在母亲怀里睡着了,但心里总还惦记着年糕,时而会醒来问母亲,熟了吗?母亲垂头看着我说,快了!看着母亲那机械地往灶膛添柴的小手和满脸的倦容,少年的我,总觉得母亲太累……凌晨时分,母亲叫醒我,切下第一块年糕让我尝鲜,此时的我,跃雀,满足,幸福……几十年的时光一晃而过,藏在心底的那抹童真,那块年糕,成了我追忆母亲的情丝,萦绕于怀,每年回乡祭奠母亲,我总会带着年糕去……结果,木炭被抢购一空,他因此得到一笔不菲的收入。然后他用这笔收入购买了一大批新树苗,于是一个新的庄园初具规模了。几年以后,“森林庄园”再度绿意盎然。请记住:别让眼睛老去,才不会让心灵荒芜。眼睛如果老去,就无法看到希望,没有希望的人生,终将失去存在的意义。积极乐观地生活,忘掉悲伤与不幸,你一定会拥有无限的快乐。当你沉湎于曾经的悲痛时,也将失去今日的欢愉。挫折和痛苦来临之时,也许正是通往成功的开始。 我们吃了中饭出来到海边去。(这是英国康槐尔极南的一角,三面是大西洋)。勖丽丽的叫响从我们的脚底下匀匀的往上颤,齐着腰,到了肩高,过了头顶,高入了云,高出了云。啊!你能不能把一种急震的乐音想象成一阵光明的细雨,从蓝天里冲着这平铺着青绿的地面不住的下?不,那雨点都是跳舞的小脚,安琪儿的。云雀们也吃过了饭,离开了它们卑微的地巢飞往高处做工去。上帝给它们的工作,替上帝做的工作。瞧着,这儿一只,那边又起了两!一起就冲着天顶飞,小翅膀活动的多快活,圆圆的,不踌躇的飞,——它们就认识青天。一起就开口唱,小嗓子活动的多快活,一颗颗小精圆珠子直往外唾,亮亮的唾,脆脆的唾,——它们赞美的是青天。瞧着,这飞得多高,有豆子大,有芝麻大,黑刺刺的一屑,直顶着无底的天顶细细的摇,——这全看不见了,影子都没了!但这光明的细雨还是不住的下着…… 飞。“其翼若垂天之云……背负苍天,而莫之夭阏者;”那不容易见着。
在五年前大国所需的镍矿基本都从亚洲人口大国印尼进口,毕竟这国镍矿物资丰富,没想到的是后印尼宣布不再出口镍矿,着实打了我方一个措手不及,万般无奈之下只能另寻其他供应商,比起不得人心的美国,我方寻找起供应商来远比美国轻松几分,菲律宾提出愿意出口镍矿给我们国家,这才解决了困扰我方的难题,据9月12日报道,印尼又开始限制镍矿出口。
假如这时候窗子外有雪——街上,城墙上,屋脊上,都是雪,胡同口一家屋檐下偎着一个戴黑兜帽的巡警,半拢着睡眼,看棉团似的雪花在半空中跳着玩……假如这夜是一个深极了的啊,不是壁上挂钟的时针指示给我们看的深夜,这深就比是一个山洞的深,一个往下钻螺旋形的山洞的深…… 假如我能有这样一个深夜,它那无底的阴森捻起我遍体的毫管;再能有窗子外不住往下筛的雪,筛淡了远近间飏动的市谣;筛泯了在泥道上挣扎的车轮;筛灭了脑壳中不妥协的潜流…… 我要那深,我要那静。那在树荫浓密处躲着的夜鹰,轻易不敢在天光还在照亮时出来睁眼。思想:它也得等。 青天里有一点子黑的。正冲着太阳耀眼,望不真,你把手遮着眼,对着那两株树缝里瞧,黑的,有榧子来大,不,有桃子来大——嘿,又移着往西了!一夜之间,一场雷电引发的山火烧毁了美丽的“森林庄园”,刚刚从祖父那里继承了这座庄园的保罗·迪克陷入了一筹莫展的境地。他经受不起打击,闭门不出,茶饭不思,眼睛熬出了血丝。一个多月过去了,年已古稀的外祖母获悉此事,意味深长地对保罗说:“小伙子,庄园成了废墟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你的眼睛失去了光泽,一天一天地老去。一双老去的眼睛,怎么能看得见希望?”保罗在外祖母的劝说下,一个人走出了庄园。他漫无目的地闲逛,在一条街道的拐弯处,他看到一家店铺的门前人头攒动,原来是一些家庭主妇正在排队购买木炭。那一块块躺在纸箱里的木炭忽然让保罗的眼睛一亮,使他看到了一线希望。于是在接下来的两个星期里,保罗雇了几名烧炭工,将庄园里烧焦的树木加工成优质的木炭,送到集市上的木炭经销店。腊月回乡祭祖,在老家逗留了几日,临别出山那天,堂弟送了我一盒年糕。所谓年糕,其寓意乃年年高的意思。按习俗,年糕是过年必备食物,平日鲜见,只有临近春节,才有它的身影。孩提时代,我最喜爱过年,每逢辞旧迎新之时,除了点炮竹,换新符、穿新衣外。还有一道难忘的口福,便是品尝母亲亲手蒸制的年糕,嚼起来甜滋滋,软绵绵,圆润鲜美,馋涎不止。说实话,母亲心灵手巧,是制作年糕的一把好手,每逢到了腊月廿四,母亲便着手这项工作,从备料到加工,都作了精细准备。记得每年秋后,母亲就托人从老家捎回一些粳米,这些米属单季稻,由于生长周期长,质软粘性好,是制糕的上等原料,如果再配加一些上好的糯米,做出来的年糕,口感香软爽滑。想当年,制做年糕全凭手工操作,即便磨粉这样重体力的活,也要靠最原始的石盘磨碾,一人推磨,一人往石盘上面的圆孔里撮撒米料,干起来即费时又费力,所以这些事,平常都属于男人干的,而我家例外,由于父亲长年被流放在外,只能由母亲独担。现在回忆起来,很难想象当年的母亲,以她那瘦弱之躯去完成这样一件工作。母亲推碾磨粉,力小速缓,有时不得已靠两手轮换使力,右手累了换左手,左手累了换右手,虽说磨盘转速缓慢,却未停歇。站在一旁的我,总要伸出助力的小手,拼力帮母亲推一把,希望替母亲省些气力。当一抹抹被碾碎的粉末,从磨盘的缝隙细细渗出,悄然地散落到沟槽中。看着那些粉未慢慢积堆起来,母亲的汗水顺着脸颊一直不断地滴落在地上。那暗淡的灯光,照着她满身疲累的背影……磨完粉,母亲将粉料放置大盆里,注入红糖水,调搅成稠糊状,用大木勺舀出,平摊入蒸笼内,中间还嵌放一些猪肉条或脱核红枣。加工年糕的蒸笼是竹制的,有三四层高,层与层之间用竹管连通蒸汽。蒸制年糕很费时,用木柴烧制,须花七八个小时。烧制一般从下午至午夜凌晨结束,这是一段最惬意的时间,吃罢晚饭,我偎依在母亲旁边,靠着灶堂口,借着柴火透出余温烤暖,一边听着母亲讲故事,一边看着干柴燃烧迸发的啪啪火星,心里盼着年糕早点出笼解馋,到了午夜时分,我瞌睡上来偎在母亲怀里睡着了,但心里总还惦记着年糕,时而会醒来问母亲,熟了吗?母亲垂头看着我说,快了!看着母亲那机械地往灶膛添柴的小手和满脸的倦容,少年的我,总觉得母亲太累……凌晨时分,母亲叫醒我,切下第一块年糕让我尝鲜,此时的我,跃雀,满足,幸福……几十年的时光一晃而过,藏在心底的那抹童真,那块年糕,成了我追忆母亲的情丝,萦绕于怀,每年回乡祭奠母亲,我总会带着年糕去……结果,木炭被抢购一空,他因此得到一笔不菲的收入。然后他用这笔收入购买了一大批新树苗,于是一个新的庄园初具规模了。几年以后,“森林庄园”再度绿意盎然。请记住:别让眼睛老去,才不会让心灵荒芜。眼睛如果老去,就无法看到希望,没有希望的人生,终将失去存在的意义。积极乐观地生活,忘掉悲伤与不幸,你一定会拥有无限的快乐。当你沉湎于曾经的悲痛时,也将失去今日的欢愉。挫折和痛苦来临之时,也许正是通往成功的开始。 我们吃了中饭出来到海边去。(这是英国康槐尔极南的一角,三面是大西洋)。勖丽丽的叫响从我们的脚底下匀匀的往上颤,齐着腰,到了肩高,过了头顶,高入了云,高出了云。啊!你能不能把一种急震的乐音想象成一阵光明的细雨,从蓝天里冲着这平铺着青绿的地面不住的下?不,那雨点都是跳舞的小脚,安琪儿的。云雀们也吃过了饭,离开了它们卑微的地巢飞往高处做工去。上帝给它们的工作,替上帝做的工作。瞧着,这儿一只,那边又起了两!一起就冲着天顶飞,小翅膀活动的多快活,圆圆的,不踌躇的飞,——它们就认识青天。一起就开口唱,小嗓子活动的多快活,一颗颗小精圆珠子直往外唾,亮亮的唾,脆脆的唾,——它们赞美的是青天。瞧着,这飞得多高,有豆子大,有芝麻大,黑刺刺的一屑,直顶着无底的天顶细细的摇,——这全看不见了,影子都没了!但这光明的细雨还是不住的下着…… 飞。“其翼若垂天之云……背负苍天,而莫之夭阏者;”那不容易见着。假如这时候窗子外有雪——街上,城墙上,屋脊上,都是雪,胡同口一家屋檐下偎着一个戴黑兜帽的巡警,半拢着睡眼,看棉团似的雪花在半空中跳着玩……假如这夜是一个深极了的啊,不是壁上挂钟的时针指示给我们看的深夜,这深就比是一个山洞的深,一个往下钻螺旋形的山洞的深…… 假如我能有这样一个深夜,它那无底的阴森捻起我遍体的毫管;再能有窗子外不住往下筛的雪,筛淡了远近间飏动的市谣;筛泯了在泥道上挣扎的车轮;筛灭了脑壳中不妥协的潜流…… 我要那深,我要那静。那在树荫浓密处躲着的夜鹰,轻易不敢在天光还在照亮时出来睁眼。思想:它也得等。 青天里有一点子黑的。正冲着太阳耀眼,望不真,你把手遮着眼,对着那两株树缝里瞧,黑的,有榧子来大,不,有桃子来大——嘿,又移着往西了!一夜之间,一场雷电引发的山火烧毁了美丽的“森林庄园”,刚刚从祖父那里继承了这座庄园的保罗·迪克陷入了一筹莫展的境地。他经受不起打击,闭门不出,茶饭不思,眼睛熬出了血丝。一个多月过去了,年已古稀的外祖母获悉此事,意味深长地对保罗说:“小伙子,庄园成了废墟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你的眼睛失去了光泽,一天一天地老去。一双老去的眼睛,怎么能看得见希望?”保罗在外祖母的劝说下,一个人走出了庄园。他漫无目的地闲逛,在一条街道的拐弯处,他看到一家店铺的门前人头攒动,原来是一些家庭主妇正在排队购买木炭。那一块块躺在纸箱里的木炭忽然让保罗的眼睛一亮,使他看到了一线希望。于是在接下来的两个星期里,保罗雇了几名烧炭工,将庄园里烧焦的树木加工成优质的木炭,送到集市上的木炭经销店。腊月回乡祭祖,在老家逗留了几日,临别出山那天,堂弟送了我一盒年糕。所谓年糕,其寓意乃年年高的意思。按习俗,年糕是过年必备食物,平日鲜见,只有临近春节,才有它的身影。孩提时代,我最喜爱过年,每逢辞旧迎新之时,除了点炮竹,换新符、穿新衣外。还有一道难忘的口福,便是品尝母亲亲手蒸制的年糕,嚼起来甜滋滋,软绵绵,圆润鲜美,馋涎不止。说实话,母亲心灵手巧,是制作年糕的一把好手,每逢到了腊月廿四,母亲便着手这项工作,从备料到加工,都作了精细准备。记得每年秋后,母亲就托人从老家捎回一些粳米,这些米属单季稻,由于生长周期长,质软粘性好,是制糕的上等原料,如果再配加一些上好的糯米,做出来的年糕,口感香软爽滑。想当年,制做年糕全凭手工操作,即便磨粉这样重体力的活,也要靠最原始的石盘磨碾,一人推磨,一人往石盘上面的圆孔里撮撒米料,干起来即费时又费力,所以这些事,平常都属于男人干的,而我家例外,由于父亲长年被流放在外,只能由母亲独担。现在回忆起来,很难想象当年的母亲,以她那瘦弱之躯去完成这样一件工作。母亲推碾磨粉,力小速缓,有时不得已靠两手轮换使力,右手累了换左手,左手累了换右手,虽说磨盘转速缓慢,却未停歇。站在一旁的我,总要伸出助力的小手,拼力帮母亲推一把,希望替母亲省些气力。当一抹抹被碾碎的粉末,从磨盘的缝隙细细渗出,悄然地散落到沟槽中。看着那些粉未慢慢积堆起来,母亲的汗水顺着脸颊一直不断地滴落在地上。那暗淡的灯光,照着她满身疲累的背影……磨完粉,母亲将粉料放置大盆里,注入红糖水,调搅成稠糊状,用大木勺舀出,平摊入蒸笼内,中间还嵌放一些猪肉条或脱核红枣。加工年糕的蒸笼是竹制的,有三四层高,层与层之间用竹管连通蒸汽。蒸制年糕很费时,用木柴烧制,须花七八个小时。烧制一般从下午至午夜凌晨结束,这是一段最惬意的时间,吃罢晚饭,我偎依在母亲旁边,靠着灶堂口,借着柴火透出余温烤暖,一边听着母亲讲故事,一边看着干柴燃烧迸发的啪啪火星,心里盼着年糕早点出笼解馋,到了午夜时分,我瞌睡上来偎在母亲怀里睡着了,但心里总还惦记着年糕,时而会醒来问母亲,熟了吗?母亲垂头看着我说,快了!看着母亲那机械地往灶膛添柴的小手和满脸的倦容,少年的我,总觉得母亲太累……凌晨时分,母亲叫醒我,切下第一块年糕让我尝鲜,此时的我,跃雀,满足,幸福……几十年的时光一晃而过,藏在心底的那抹童真,那块年糕,成了我追忆母亲的情丝,萦绕于怀,每年回乡祭奠母亲,我总会带着年糕去……结果,木炭被抢购一空,他因此得到一笔不菲的收入。然后他用这笔收入购买了一大批新树苗,于是一个新的庄园初具规模了。几年以后,“森林庄园”再度绿意盎然。请记住:别让眼睛老去,才不会让心灵荒芜。眼睛如果老去,就无法看到希望,没有希望的人生,终将失去存在的意义。积极乐观地生活,忘掉悲伤与不幸,你一定会拥有无限的快乐。当你沉湎于曾经的悲痛时,也将失去今日的欢愉。挫折和痛苦来临之时,也许正是通往成功的开始。 我们吃了中饭出来到海边去。(这是英国康槐尔极南的一角,三面是大西洋)。勖丽丽的叫响从我们的脚底下匀匀的往上颤,齐着腰,到了肩高,过了头顶,高入了云,高出了云。啊!你能不能把一种急震的乐音想象成一阵光明的细雨,从蓝天里冲着这平铺着青绿的地面不住的下?不,那雨点都是跳舞的小脚,安琪儿的。云雀们也吃过了饭,离开了它们卑微的地巢飞往高处做工去。上帝给它们的工作,替上帝做的工作。瞧着,这儿一只,那边又起了两!一起就冲着天顶飞,小翅膀活动的多快活,圆圆的,不踌躇的飞,——它们就认识青天。一起就开口唱,小嗓子活动的多快活,一颗颗小精圆珠子直往外唾,亮亮的唾,脆脆的唾,——它们赞美的是青天。瞧着,这飞得多高,有豆子大,有芝麻大,黑刺刺的一屑,直顶着无底的天顶细细的摇,——这全看不见了,影子都没了!但这光明的细雨还是不住的下着…… 飞。“其翼若垂天之云……背负苍天,而莫之夭阏者;”那不容易见着。假如这时候窗子外有雪——街上,城墙上,屋脊上,都是雪,胡同口一家屋檐下偎着一个戴黑兜帽的巡警,半拢着睡眼,看棉团似的雪花在半空中跳着玩……假如这夜是一个深极了的啊,不是壁上挂钟的时针指示给我们看的深夜,这深就比是一个山洞的深,一个往下钻螺旋形的山洞的深…… 假如我能有这样一个深夜,它那无底的阴森捻起我遍体的毫管;再能有窗子外不住往下筛的雪,筛淡了远近间飏动的市谣;筛泯了在泥道上挣扎的车轮;筛灭了脑壳中不妥协的潜流…… 我要那深,我要那静。那在树荫浓密处躲着的夜鹰,轻易不敢在天光还在照亮时出来睁眼。思想:它也得等。 青天里有一点子黑的。正冲着太阳耀眼,望不真,你把手遮着眼,对着那两株树缝里瞧,黑的,有榧子来大,不,有桃子来大——嘿,又移着往西了!一夜之间,一场雷电引发的山火烧毁了美丽的“森林庄园”,刚刚从祖父那里继承了这座庄园的保罗·迪克陷入了一筹莫展的境地。他经受不起打击,闭门不出,茶饭不思,眼睛熬出了血丝。一个多月过去了,年已古稀的外祖母获悉此事,意味深长地对保罗说:“小伙子,庄园成了废墟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你的眼睛失去了光泽,一天一天地老去。一双老去的眼睛,怎么能看得见希望?”保罗在外祖母的劝说下,一个人走出了庄园。他漫无目的地闲逛,在一条街道的拐弯处,他看到一家店铺的门前人头攒动,原来是一些家庭主妇正在排队购买木炭。那一块块躺在纸箱里的木炭忽然让保罗的眼睛一亮,使他看到了一线希望。于是在接下来的两个星期里,保罗雇了几名烧炭工,将庄园里烧焦的树木加工成优质的木炭,送到集市上的木炭经销店。腊月回乡祭祖,在老家逗留了几日,临别出山那天,堂弟送了我一盒年糕。所谓年糕,其寓意乃年年高的意思。按习俗,年糕是过年必备食物,平日鲜见,只有临近春节,才有它的身影。孩提时代,我最喜爱过年,每逢辞旧迎新之时,除了点炮竹,换新符、穿新衣外。还有一道难忘的口福,便是品尝母亲亲手蒸制的年糕,嚼起来甜滋滋,软绵绵,圆润鲜美,馋涎不止。说实话,母亲心灵手巧,是制作年糕的一把好手,每逢到了腊月廿四,母亲便着手这项工作,从备料到加工,都作了精细准备。记得每年秋后,母亲就托人从老家捎回一些粳米,这些米属单季稻,由于生长周期长,质软粘性好,是制糕的上等原料,如果再配加一些上好的糯米,做出来的年糕,口感香软爽滑。想当年,制做年糕全凭手工操作,即便磨粉这样重体力的活,也要靠最原始的石盘磨碾,一人推磨,一人往石盘上面的圆孔里撮撒米料,干起来即费时又费力,所以这些事,平常都属于男人干的,而我家例外,由于父亲长年被流放在外,只能由母亲独担。现在回忆起来,很难想象当年的母亲,以她那瘦弱之躯去完成这样一件工作。母亲推碾磨粉,力小速缓,有时不得已靠两手轮换使力,右手累了换左手,左手累了换右手,虽说磨盘转速缓慢,却未停歇。站在一旁的我,总要伸出助力的小手,拼力帮母亲推一把,希望替母亲省些气力。当一抹抹被碾碎的粉末,从磨盘的缝隙细细渗出,悄然地散落到沟槽中。看着那些粉未慢慢积堆起来,母亲的汗水顺着脸颊一直不断地滴落在地上。那暗淡的灯光,照着她满身疲累的背影……磨完粉,母亲将粉料放置大盆里,注入红糖水,调搅成稠糊状,用大木勺舀出,平摊入蒸笼内,中间还嵌放一些猪肉条或脱核红枣。加工年糕的蒸笼是竹制的,有三四层高,层与层之间用竹管连通蒸汽。蒸制年糕很费时,用木柴烧制,须花七八个小时。烧制一般从下午至午夜凌晨结束,这是一段最惬意的时间,吃罢晚饭,我偎依在母亲旁边,靠着灶堂口,借着柴火透出余温烤暖,一边听着母亲讲故事,一边看着干柴燃烧迸发的啪啪火星,心里盼着年糕早点出笼解馋,到了午夜时分,我瞌睡上来偎在母亲怀里睡着了,但心里总还惦记着年糕,时而会醒来问母亲,熟了吗?母亲垂头看着我说,快了!看着母亲那机械地往灶膛添柴的小手和满脸的倦容,少年的我,总觉得母亲太累……凌晨时分,母亲叫醒我,切下第一块年糕让我尝鲜,此时的我,跃雀,满足,幸福……几十年的时光一晃而过,藏在心底的那抹童真,那块年糕,成了我追忆母亲的情丝,萦绕于怀,每年回乡祭奠母亲,我总会带着年糕去……结果,木炭被抢购一空,他因此得到一笔不菲的收入。然后他用这笔收入购买了一大批新树苗,于是一个新的庄园初具规模了。几年以后,“森林庄园”再度绿意盎然。请记住:别让眼睛老去,才不会让心灵荒芜。眼睛如果老去,就无法看到希望,没有希望的人生,终将失去存在的意义。积极乐观地生活,忘掉悲伤与不幸,你一定会拥有无限的快乐。当你沉湎于曾经的悲痛时,也将失去今日的欢愉。挫折和痛苦来临之时,也许正是通往成功的开始。 我们吃了中饭出来到海边去。(这是英国康槐尔极南的一角,三面是大西洋)。勖丽丽的叫响从我们的脚底下匀匀的往上颤,齐着腰,到了肩高,过了头顶,高入了云,高出了云。啊!你能不能把一种急震的乐音想象成一阵光明的细雨,从蓝天里冲着这平铺着青绿的地面不住的下?不,那雨点都是跳舞的小脚,安琪儿的。云雀们也吃过了饭,离开了它们卑微的地巢飞往高处做工去。上帝给它们的工作,替上帝做的工作。瞧着,这儿一只,那边又起了两!一起就冲着天顶飞,小翅膀活动的多快活,圆圆的,不踌躇的飞,——它们就认识青天。一起就开口唱,小嗓子活动的多快活,一颗颗小精圆珠子直往外唾,亮亮的唾,脆脆的唾,——它们赞美的是青天。瞧着,这飞得多高,有豆子大,有芝麻大,黑刺刺的一屑,直顶着无底的天顶细细的摇,——这全看不见了,影子都没了!但这光明的细雨还是不住的下着…… 飞。“其翼若垂天之云……背负苍天,而莫之夭阏者;”那不容易见着。假如这时候窗子外有雪——街上,城墙上,屋脊上,都是雪,胡同口一家屋檐下偎着一个戴黑兜帽的巡警,半拢着睡眼,看棉团似的雪花在半空中跳着玩……假如这夜是一个深极了的啊,不是壁上挂钟的时针指示给我们看的深夜,这深就比是一个山洞的深,一个往下钻螺旋形的山洞的深…… 假如我能有这样一个深夜,它那无底的阴森捻起我遍体的毫管;再能有窗子外不住往下筛的雪,筛淡了远近间飏动的市谣;筛泯了在泥道上挣扎的车轮;筛灭了脑壳中不妥协的潜流…… 我要那深,我要那静。那在树荫浓密处躲着的夜鹰,轻易不敢在天光还在照亮时出来睁眼。思想:它也得等。 青天里有一点子黑的。正冲着太阳耀眼,望不真,你把手遮着眼,对着那两株树缝里瞧,黑的,有榧子来大,不,有桃子来大——嘿,又移着往西了!一夜之间,一场雷电引发的山火烧毁了美丽的“森林庄园”,刚刚从祖父那里继承了这座庄园的保罗·迪克陷入了一筹莫展的境地。他经受不起打击,闭门不出,茶饭不思,眼睛熬出了血丝。一个多月过去了,年已古稀的外祖母获悉此事,意味深长地对保罗说:“小伙子,庄园成了废墟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你的眼睛失去了光泽,一天一天地老去。一双老去的眼睛,怎么能看得见希望?”保罗在外祖母的劝说下,一个人走出了庄园。他漫无目的地闲逛,在一条街道的拐弯处,他看到一家店铺的门前人头攒动,原来是一些家庭主妇正在排队购买木炭。那一块块躺在纸箱里的木炭忽然让保罗的眼睛一亮,使他看到了一线希望。于是在接下来的两个星期里,保罗雇了几名烧炭工,将庄园里烧焦的树木加工成优质的木炭,送到集市上的木炭经销店。腊月回乡祭祖,在老家逗留了几日,临别出山那天,堂弟送了我一盒年糕。所谓年糕,其寓意乃年年高的意思。按习俗,年糕是过年必备食物,平日鲜见,只有临近春节,才有它的身影。孩提时代,我最喜爱过年,每逢辞旧迎新之时,除了点炮竹,换新符、穿新衣外。还有一道难忘的口福,便是品尝母亲亲手蒸制的年糕,嚼起来甜滋滋,软绵绵,圆润鲜美,馋涎不止。说实话,母亲心灵手巧,是制作年糕的一把好手,每逢到了腊月廿四,母亲便着手这项工作,从备料到加工,都作了精细准备。记得每年秋后,母亲就托人从老家捎回一些粳米,这些米属单季稻,由于生长周期长,质软粘性好,是制糕的上等原料,如果再配加一些上好的糯米,做出来的年糕,口感香软爽滑。想当年,制做年糕全凭手工操作,即便磨粉这样重体力的活,也要靠最原始的石盘磨碾,一人推磨,一人往石盘上面的圆孔里撮撒米料,干起来即费时又费力,所以这些事,平常都属于男人干的,而我家例外,由于父亲长年被流放在外,只能由母亲独担。现在回忆起来,很难想象当年的母亲,以她那瘦弱之躯去完成这样一件工作。母亲推碾磨粉,力小速缓,有时不得已靠两手轮换使力,右手累了换左手,左手累了换右手,虽说磨盘转速缓慢,却未停歇。站在一旁的我,总要伸出助力的小手,拼力帮母亲推一把,希望替母亲省些气力。当一抹抹被碾碎的粉末,从磨盘的缝隙细细渗出,悄然地散落到沟槽中。看着那些粉未慢慢积堆起来,母亲的汗水顺着脸颊一直不断地滴落在地上。那暗淡的灯光,照着她满身疲累的背影……磨完粉,母亲将粉料放置大盆里,注入红糖水,调搅成稠糊状,用大木勺舀出,平摊入蒸笼内,中间还嵌放一些猪肉条或脱核红枣。加工年糕的蒸笼是竹制的,有三四层高,层与层之间用竹管连通蒸汽。蒸制年糕很费时,用木柴烧制,须花七八个小时。烧制一般从下午至午夜凌晨结束,这是一段最惬意的时间,吃罢晚饭,我偎依在母亲旁边,靠着灶堂口,借着柴火透出余温烤暖,一边听着母亲讲故事,一边看着干柴燃烧迸发的啪啪火星,心里盼着年糕早点出笼解馋,到了午夜时分,我瞌睡上来偎在母亲怀里睡着了,但心里总还惦记着年糕,时而会醒来问母亲,熟了吗?母亲垂头看着我说,快了!看着母亲那机械地往灶膛添柴的小手和满脸的倦容,少年的我,总觉得母亲太累……凌晨时分,母亲叫醒我,切下第一块年糕让我尝鲜,此时的我,跃雀,满足,幸福……几十年的时光一晃而过,藏在心底的那抹童真,那块年糕,成了我追忆母亲的情丝,萦绕于怀,每年回乡祭奠母亲,我总会带着年糕去……结果,木炭被抢购一空,他因此得到一笔不菲的收入。然后他用这笔收入购买了一大批新树苗,于是一个新的庄园初具规模了。几年以后,“森林庄园”再度绿意盎然。请记住:别让眼睛老去,才不会让心灵荒芜。眼睛如果老去,就无法看到希望,没有希望的人生,终将失去存在的意义。积极乐观地生活,忘掉悲伤与不幸,你一定会拥有无限的快乐。当你沉湎于曾经的悲痛时,也将失去今日的欢愉。挫折和痛苦来临之时,也许正是通往成功的开始。 我们吃了中饭出来到海边去。(这是英国康槐尔极南的一角,三面是大西洋)。勖丽丽的叫响从我们的脚底下匀匀的往上颤,齐着腰,到了肩高,过了头顶,高入了云,高出了云。啊!你能不能把一种急震的乐音想象成一阵光明的细雨,从蓝天里冲着这平铺着青绿的地面不住的下?不,那雨点都是跳舞的小脚,安琪儿的。云雀们也吃过了饭,离开了它们卑微的地巢飞往高处做工去。上帝给它们的工作,替上帝做的工作。瞧着,这儿一只,那边又起了两!一起就冲着天顶飞,小翅膀活动的多快活,圆圆的,不踌躇的飞,——它们就认识青天。一起就开口唱,小嗓子活动的多快活,一颗颗小精圆珠子直往外唾,亮亮的唾,脆脆的唾,——它们赞美的是青天。瞧着,这飞得多高,有豆子大,有芝麻大,黑刺刺的一屑,直顶着无底的天顶细细的摇,——这全看不见了,影子都没了!但这光明的细雨还是不住的下着…… 飞。“其翼若垂天之云……背负苍天,而莫之夭阏者;”那不容易见着。
自从几年前印尼不再出口镍矿后,时隔三年后该国自己撤回了禁令,宣布恢复对外出口,而我方深谙一个鸡蛋最好别放同一篮子的道理,这样最大程度上能规避风险,中方和菲律宾保持合作的同时也恢复了和印尼的镍矿往来,但却不及以前那么依赖,毕竟印尼有中断合作的“前科”,没想到的是不出中方所料,印尼又突然宣布后不再出口镍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