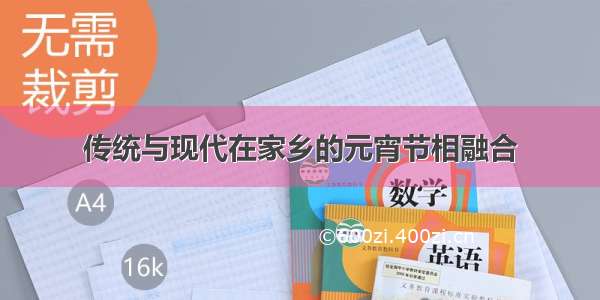封面图credit to:谢姗姗
如果说,一切的开始是在三年前的那个若阴若晴的冬天,那么一切的结束,就在六月一天的下午四点发生了。
那是在Queens楼顶的大阳台上,风很大,天上的云越积越多,Silver street上一如既往地游人如织,一切的底色还是六月该有的那种阳光。阳台上有一张桌子和几把木椅,桌上有两瓶香槟和两袋零食,即使天气已经暖和起来,他还是一身西装笔挺。“喝点什么?”他拿起一只高脚杯递过来。
两个小时的对话之后,大家慢慢陷入了沉默,彼此无言地点着头。忘了是谁缓缓起身,说有点事要先离开了。Maarten抬手看看表,说,也是时候了,都走吧都走吧。我们都站起来。他微微鞠躬:“和你们度过的这一年不能更棒了。日后多保重。”我们垂首,杂七杂八地低声回答:“你也是。”Gail推开门,我们鱼贯而出的时候,我从他的墨镜里看到了天光的倒影。
一
这样的对话,当然,迟早会发生,但我从没想到它们会这样早发生。有关于这种提前,两个月前我是这样写的:
“四月中回了剑桥,学期开始前不久,一天的暮色里,我习惯性地打开邮箱,看到我的DoS,我最爱也最重要的导师,发信说他夏天要离开剑桥了。我把页面停在末尾,反复读了三遍没有出错,然后摘下眼镜,全身开始颤抖起来。有那么一瞬间,我还认为那一晚我还可以复习一点东西,但不必很久我就意识到了自己的错误。我夺门而出,泪水潸潸而下。
“我跑去屋后的树林和花园里,四下黑暗无人,我不必掩饰自己的悲伤,也不必强忍泪水。上次情感崩溃到如此地步已经是好久好久以前了,我想。我想找人倾诉,可是朋友们即便理解我的痛苦,没有人可以和我共情。他们说,他们和他们DoS之间的关系完全不是这么回事儿,你和你DoS之间太特别了;一些日子以前,他们还说,我和他之间的关系,像是暗恋和被暗恋,舔狗和女神。
“那时候,调侃归调侃,心里想的总是由他去,我和Maarten的关系确实非比寻常,我也确实对他太过喜爱,听他们说着,总觉得有种师生之间的友谊,是我的幸运。可是它就要这样结束了啊。前些日子我还想,如果读研他还可以是我的导师,这或许会给我很大动力尝试留下来吧?可是这样的念想也断了啊。我从最初的面试,想到开学时的见面,想到那些supervision,再到philosopher formal和那之后酒吧里的谈天。或许日后有机会,我会认真把那些都详细写下来。对我这样的人而言,写下来,才算是彻底地画上句号。可是我总是迟迟不愿下笔啊,仿佛那个句号还没落成,他也就还不会离开。”
如今挥别之后,大约就是时候落笔写下这个句号了。我的勇气和决心都来源于,也只能来源于时间:在那一切发生的两个月之后,想到日后不能再坐在他对面聊天,终于能够不再心中绞痛了。
二
一切的开始,是的冬天。我还能回忆起妈那阵子说的,英国真是个雾蒙蒙的国家——那想必那天的剑桥是稍有点阴、稍有点雾气的。那时候的Queens对我还陌生,雾气或许还让古老的红砖墙,和墙上优雅的爬墙虎显得有一点古远的神秘。我走到面试约定的屋门口,那里脚下的地板每走一步都吱呀作响,我怯生生地不敢使劲迈步,在门前踌躇,也不知该不该敲门。
他准点打开了门,邀我进去。那时他的胡子修得很精致,戴着琥珀色的圆眼镜,双眼蓝得很深邃,鼻子高而尖,让人想起某种北欧的精灵。他旋开门把手,把我请进里屋,然后在长沙发上相对坐下。然后,奇迹般地,在他给我倒了杯水、闲聊一点生活的工夫,在门外的等待中积蓄起来的紧张就都烟消云散了。他动作和话语的每个细节、每一句会被当成是在客套的问候,都在倾诉一种不容置疑的友好,在这种友好的氛围里,紧张如我也慢慢松弛下来,有问有答,侃侃而谈。有人说,这世上有人本就是拥有那样的气质的,而我如此幸运,第一次遇到这样的人,竟然是在一场面试里。
寒暄过后,他说,你看,坐的舒服点,那我们开始聊天吧。你说,计算机会拥有意识吗?如果足够复杂,它有可能像人类一样感受到爱与恨、快乐与痛苦吗?
然后半个小时过去。那半个小时收获颇丰——那是一个小有成就的年轻哲学家,带着一个半只脚刚刚踏入门的新手,从高空游历了一圈哲学王国的领地。落地的时候,他说,这两天在剑桥去伦敦好好玩玩,忘掉哲学吧,你前些日子学得一定够辛苦了。而从那个古老的屋子出来的时候,我想,如果之后还有机会,我一定要告诉他,那一天我之所以能有让自己无悔的发挥,实在要归功于他的成全。而幸运地,后来,我也真的有了告诉他的机会。一年半以后,我以正式学生的身份来到Queens"的时候,首先期待的,就是再次和他见面。而那已是的十月了。
三
十月的天气凉热正好,刚来到剑桥时候,整个人面临着一种完全不同的生活环境,整天生活在强烈的焦虑之下——一切都还没形成习惯,生活节奏也好,跟人打交道的方式也罢,所有的事情尚需要慢慢摸索,一切尚不确定,不确定派生焦虑;焦虑从刚住下来开始缓缓积累,积累到顶峰而向下转折,是在十月三日:那天上午,所有人都在见DoS,所有人仿佛几天前都受到了见面的时间地点,唯独我再三检查邮箱,也没信。我战战兢兢地去邮件问他,他总算回复:还有这回事儿呢!那我们就今天下午见好了。
准点到了他办公室门口,我敲敲门,他像从前那样起身把门打开,伸出手来:欢迎回到这里,好久不见了。这些天适应得如何?那时候同他尚不熟稔,可当他这么一问,我也没禁住把生活上种种难处倾倒出去——毕竟那时候也没其他人可以倾诉。他就合着手静静地听,时不时点点头。等我说完了,他也跟我讲起他刚来英国时的难处,他来自荷兰,刚来读研时英语也不那么娴熟,一旦环境嘈杂,身边人说的是什么完全听不懂。——可自己不还是如此这般过来了么!何况荷兰语和英语一定比中文英文之间相似得多。
第一次见面就这样聊了闲天,他跟我说当年是怎么一点点走过来的,有什么有用的建议,听着心情慢慢舒解下来。最后几分钟回到正题,学习的事,他扔了篇论文题给我,说下次再聊便了。正当我要转身出门,他忽然喊住我:对了!你和Gail这些天什么时候有空?带你们去趟Queens 15世纪的老图书馆,看看笛卡尔那本第一沉思录在欧洲的初版,看看那些活了五百多年的书是什么样子。如何?
我跳起来:随时!
四
第一学期期末要回国打辩论——那是从天上掉下馅饼来的新国辩,有机会轮到我,当然很快决意要去。可那样会耽误一周的课,得同DoS请假。几位学长姐请假的时候都遇到不小的难处,毕竟DoS主管学习,你要翘掉一周的课,自然要刁难你一番。
我本也做好了请假艰难的准备,准备了一番回国打比赛的重要性和理由,好去向他慷慨陈词。有天在路上遇到他,正好一起去走去上课,我借机向他请假。刚陈清事由,还没来得及发挥,他大手一挥:如果你真的这样决定了,去就是了。他看我一愣,笑着拍我肩膀:不管那是什么事情,你既然来向我请假,说明你真的觉得那重要。那我怎么好成为你追求这件事情路上的阻碍呢?至于课,自己回去看看就是,如果有看不懂的,下学期尽管约我给你讲。
后来也总是在路上遇见他,毕竟Queens到上课的地方,就那么一条小路。以前总是怕老师,遇上了觉得避之不及,可如今甚至会期盼有机会一起走去上课——只不过他最后要站到讲台上,而我要坐在课桌前。路上有时也谈哲学,有时也谈文化,他也总追着问我辩题是什么,可我总没法把“直男癌”翻译给他,只能很模糊地说事关性别平等;又听说会上电视一类,他还兴奋地问他能不能看得到,一气说完才反应过来,中文辩论他看着也是一头雾水,于是轻轻一笑带过去。
第一学期结束后,忙完辩论,回到家里,我这样写他:
“从他的言谈看,对他来说,一个哲学家最重要的,是宽容与开放的思维。Matriculation formal(入学时的正装晚餐)上同他聊天,问他面试选择我们的时候判准是什么,他的回答是,很多时候他也说不清面试标准具体是怎么回事儿,复杂得很,但有一条是他自己的硬标准:如果一个人在面试中表现出arrogance,傲慢自大,或者任何觉得自己全然正确、不愿意改变自己意见的倾向,能力再强都一定不要。一个在讨论中愿意保持开放头脑、愿意改变自己意见的人,即使他觉得尴尬也好、前后不一也罢,我会喜欢他。
“后来聊到其他的话题,提到进化论和“达尔文的新一代斗犬”理查德道金斯,他的态度颇鄙夷。他不喜欢那些头衔被冠以“斗犬”的人:人一旦好斗,就容易失去开放的头脑。他说,我不信教,但不喜欢道金斯对宗教强烈的批评,以他对神创论的攻击,甚至可能还没有触及宗教的实质。人万勿对自己太自信了。对那些鄙夷形而上的科学家如费曼,他的印象也不算好。第一次supo,我提到海森堡的不确定性原理,他笑着调侃我:Scientists tend to be very bad philosophers. 科学家大都是极糟糕的哲学家。
“后来学期末他讲课,有关因果律一类,提到是否存在simultaneous causation和backwards causation,意即原因能不能和结果同时出现甚至在结果之后,在课上提到“有些量子物理学家觉得,或许量子层面上,这两种情况完全可能。反正我们都搞不懂,似乎随他们去说,说什么是什么好了”。说到最后一句,他眼光正好扫到我,俏皮地一眨眼。我想起他调侃海森堡的那句话,那一瞬间的感觉,仿佛时间线弯曲,两个月成了一个闭环,头尾相衔。在这闭环里一直不出来,似乎也无伤大雅。”
五
此后一个学习,也常见面,见面就聊天,在路上,在院里,在晚饭桌上——于是一点点熟起来,想起什么都谈。聊音乐,他会讲他年轻时候听的那些摇滚,多像是我正在听的那些东西,而现在如何慢慢转向爵士。聊风格,餐桌上他会指着我的手表赞叹,我告诉他是北欧一个冷门牌子,他一拍手:“当然是北欧!做这种极简风的东西只有北欧做的最好。I"m a minimalist by nature.”然后他亮出他的手表,除了颜色,有关风格形貌的一切都同我那只惊人地相似。聊剑桥的文化,他会告诉我,在荷兰,给教授high table、和学生分开吃饭这种事情绝不可接受,荷兰非常讲求平等,把老师和学生分开吃饭简直会上新闻头条。而他会补充一句:“我个人倒觉得还挺有意思。人和人之间等级层次纷繁复杂固然糟糕,如果完全失去层次似乎也没意思。”
有时候,吃完formal也一起走去bar里,点一杯啤酒或者他喜欢的Gin and tonic,聊聊他在欧洲的生活,聊聊我们的家乡(荷兰和中国),聊聊他喜欢的哲学家。一点酒后他的谈兴会变得很好,逸兴遄飞。他总同我说:你看,学哲学,历史太重要了。analytic philosophy(分析哲学)不看历史,那还是差点东西。同样的概念,柏拉图说还是笛卡尔说还是当今某个哲学家说,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context下,含义天差地别。History matters. 或者,当他不那么严肃的时候,他会开始一边小口抿酒一边吐槽英国的酒文化:“如果你在英国,想要有点夜生活,无论你最初做些什么,最后都会落到酒吧里去。真是奇怪。”
如此等等,时间就这样流过去,其实平平无奇,但也分外宜人。他的渊博、他的友好,总让我心里安稳:学习上、甚至生活上,无论有什么难处,总有人在那里、他的门总是欢迎地敞开着的。我不必有什么心理压力,因为我知道他总是会审慎地措辞、审慎地选择语气和讲法,为的就是不给对话者增加任何来自他的压力。我知道如果他忘了回什么邮件,我总可以在路上抓住他提醒他的。我大量地使用“总”这个字,就是在说:在剑桥的生活中有一种让人安心的连续性,而他的存在是这种连续性的保障。
当然,后来,那种保障就失去了,正如你人生中所有可以称作“保障”的东西,最终都要失去。那句歌怎么唱的来着,“早知道伤心总是难免的,在每一个梦醒时分”。
六
得悉他要离去的第二天下午,天色向晚,从琴房出来,远远看到他的身影。我一路小跑过去,追上他,打了个招呼。我问他为什么要走,他说,系里没续约他的合同。所以,不是他能决定的事儿了——从他眼里我也能读出了一点怅然。得知这一点的我,会不会感到一点安慰呢?我问,那你定下来日后去哪儿了吗?他说,去瑞典了。我忽然想到好些天前,我们在餐桌上谈天,他同我讲述他接下来两年宏伟的学术计划。他在那里还有机会继续么?这个问题我没问出口。沉默了一会儿,我说,你真的是个很棒的DoS。我们都很喜欢你。他轻轻摇摇头,说,谢谢你告诉我这个。
北欧。他终究离开英语世界了。我想起见他第一面的时候,琢磨他的鼻子,有种北欧精灵的感觉。我想起他总跟我夸北欧的东西,夸北欧的文化和审美——北欧盛行的极简风,太合他的胃口了。也好。可瑞典话——跟他聊过语言,他也不曾提过他精通瑞典语吧?或者去那边上课仍旧用英文不成?
总之晚上胡思乱想。后一天的清晨,是学期开始与DoS见面的会议,四个学生围着他坐成一个半圆,窗外阴雨连绵。我忽然想到,在刚来剑桥不久,天气也是这样忽然降温转雨,我咳嗽着走进他的办公室,他笑着递上手纸:“欢迎来到剑桥!想必你已经对这儿的天气有了充分的体会。”
他合着手,屋子里很安静。他先开的口:“你们应该知道我要离开了。你们知道,我和系里的合同是临时合同,一年一续的那种。今年,不知道为什么,系里就是没续我的合同。或许我还不够好吧。”他苦笑一声的时候,我感觉心里被什么扎了一下。“可他还年轻啊!”我心说,“Q跟我说,他今年的lecture(讲座)比之去年是有着长足的进步啊。对于一个这么年轻的lecturer,他们还能要求什么呢?更何况,这几年他一力承下了philosophy of language(语言哲学)几乎全部的lecture,他不在了,还有谁来讲这些呢?”
“或许考完试之后...”他接下去,“我们可以安排一个party吧。我会喊上你们,也有个机会好好说一下再见...不过...不过现在你们还是好好琢磨考试的事儿吧...”后面的话,我没有再怎么听入耳,只记得雨声愈响,天色愈暗,屋里的气氛愈向下沉,直到变得难以居留,我们就一一告退。
七
又好些天过去了,有位朋友同我说,你想,毕竟剑桥厉害的人那么多,下一个DoS或许会更好呢。我说,或许是,但不重要。无论谁来,他毕竟不是Maarten。比如说,你说你喜欢一个人,然后你遇到了比她/他更漂亮/帅的人,你就移情别恋了么?那不是真正的喜欢。但这不只局限在爱情:特别的感情,总是one-one relationship。你的感情所贯注的,总是那一个特别的个体,不可替代。他就不可替代。
后来,这个学期还是约他上了几次supervision(一对一的课)。有时也不是有什么特别棘手的问题要请教他;只是想到之后再也见不到他了,总想多听听他聊哲学。也总能完全沉进去,忘了时间飞逝,本该是一个小时的supervision,常常能聊很久。从Queens最高层的supervision room往外看,绿树参天,把阳光切碎撒进屋子来,落在案头和白板上,恰好是那种气氛里最棒的作料。
出了成绩那晚在院里遇到他,即使天色向晚,他仍未摘掉他的墨镜。我说,毕竟有点遗憾啊,差那么一点点first。他说,那一点关系都没有。如果你在担忧分数不够好看,第一年的成绩是不算数的。如果你在怀疑自己做得不够好,那大可不必——你起点太低了,毕竟此前从未写过英文文章,能到如今、跨进前百分之三十,已经殊不容易。就这样下去,你明年一定可以first的。然后他低声补一句:那时候我就看不到了,不过你还要像今年一样好好努力啊。
而如果你把这篇文章想象成一部电影,一幕幕的画面匆匆闪过去,它的结尾就是在那阳台上,像《这个杀手不太冷》那样,镜头拍着我们最后那一次谈天,不断升高,不断升高,直到阳台上的每个人都变成不可见的小黑点,讲话的声音被风声吞没。然后屏幕会黑下去。那就是在说:故事结束了。
结尾或许也会有一段念白。那将是杜拉斯的那句话:将来我一生都会记得这个下午,尽管那时我甚至会忘记他的面容,忘记他的姓名。
如果还有一个彩蛋,那大约会是这样:还在严冬的时候,一天吃饭的时候遇上他,于是相对坐下闲聊。聊天的细节早都消失在时间里,但至今我仍然清晰记得的,是他说,Queens"的那片被落叶覆盖着的树林,在夏天来的时候会变成全剑桥最美的花园,最肥沃的土能长出最美的花,颜色饱满到极点鲜艳到极点。那次以后,每次去树林都抱着点希冀,期待着想象着这儿如果开遍鲜花会是怎样。
后来,已经知道离去在即,五月的某一天,复习到疲惫的时候,傍晚独自去那片树林散步。再看那花团锦簇的时候,整个人仿佛忽然被什么迎头痛击,抱着头蹲下来。你看啊,你看啊,我想,你说过最美的花都已经开了啊都已经几乎要谢了啊而你怎么就要走了啊,明年春夏的时候你就看不到了啊。你还只在Queens"看了三年的花开啊,为什么不能继续在这儿走下去呢...
而配乐,要用刺猬的《白日梦蓝》。不为别的,只为了那句后来听了千百遍的歌词:“请你不要离开,这里胜似花开。”而当花都谢了,人也就该放下了。
那就祝你一切都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