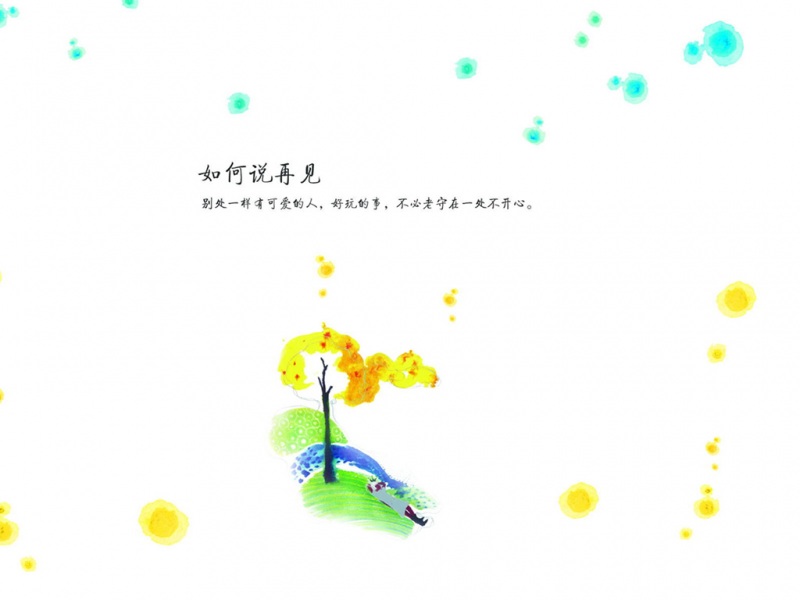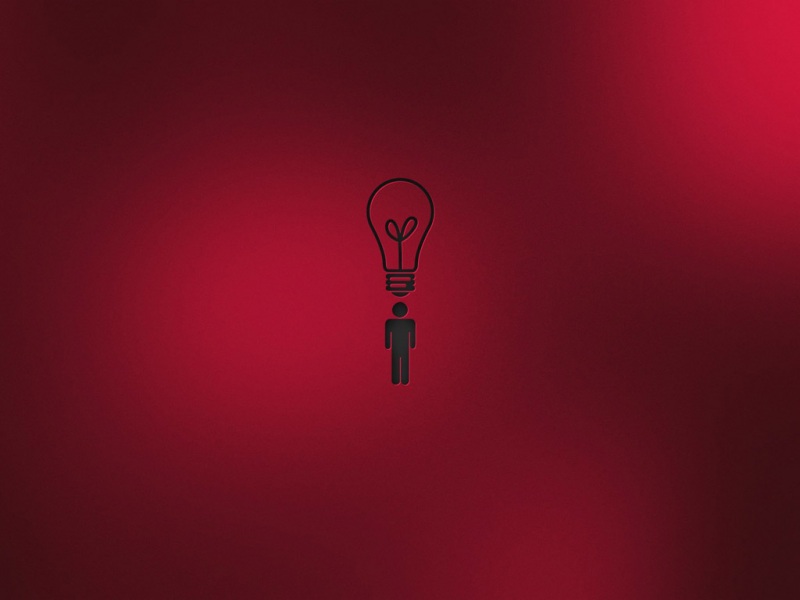07.14 19:42阅读8545
我和佩瑶是在一个party上认识的,朋友给我介绍说:辛佩瑶,刚从奥地利过来的。
她微笑着伸出手来,与我轻轻一握。
我们就此成为好朋友。佩瑶略有些内向,没人的时候她和你滔滔不绝,大家在一起聚会,她却一声不吭,人们甚至都感觉不到她的存在。
她母亲是哈尔滨人,父亲是天津人。母亲在哈尔滨教小学,父亲在天津教大学。因为工作的关系,一直分居两地。直到退休以后,母亲才到天津和父亲团聚。在这之前的十几年里,她只有在寒假暑假才能到天津去看望爸爸。
佩瑶告诉我,她从小就想出国。她爸爸有一个要好的同事,姓吴,是教古汉语的,很有学问。吴叔叔家和佩瑶家住同一个楼道,她家二楼,吴叔叔家三楼。吴叔叔十分喜欢这个漂亮小丫头,吴太太姓方,在音乐学院教钢琴,也十分喜欢佩瑶,但她说这孩子心思太乱,将来怕会在感情上遇到坎坷。
吴叔叔在奥地利有个八杆子打不着的亲戚,有一年回国来玩儿,大概吴叔叔给招待好了,回去就寄来了邀请。说实话,吴叔叔并不想去—— 满嘴平平仄仄,去奥地利干什么?倒是方老师想去,毕竟是音乐之都嘛。她撺掇吴叔叔去,以后站住脚了,她也过去看看养育莫札特的萨尔茨堡。
吴叔叔就去了。
半年后,他回了一趟国,给佩瑶带了小礼物,还有一本厚厚的影集,都是他在奥地利拍的。佩瑶一张张翻开看,吴叔叔在旁边讲解。
“这就是萨尔茨堡,莫札特的出生地。”
“这是林茨,希特勒在这里中学毕业──他是奥地利人。”
“这是皇宫,这面两条红一条白的旗子是奥地利国旗。据说奥匈帝国的一位公爵在与敌人血战时,白色的长袍被鲜血染红,只有他腰部佩剑的地方留下一道白痕。奥地利人便以此做为国旗,意即宁可战死,也不投降。”
佩瑶醉了,她放下影集:“你把我也带出去吧吴叔叔,我也要出国。”
吴叔叔笑了,“真的?”
“骗你是小狗!”
妈妈对老吴说:“别听这孩子瞎掰。”
“谁瞎掰了?我就要出国。一辈子闷在天津,那才叫崴泥!”
大家都乐了。
吴叔叔问她:“你为什么想出国呢?”
佩瑶说:“生活在别处你懂不懂啊?”
妈妈叹口气说:“没她不看的书,生给看傻了。”
禁不住她死缠,爸妈都同意了。毕竟有老吴照看着,好就呆着,不好就回来,多大点事儿。
邀请书很快寄到了,她飞到了音乐之都。
吴叔叔开车把佩瑶接到自己那两室一厅的公寓里,大房子给佩瑶住,小房子自己住。放下行李洗把脸,吴叔叔端上准备好的茶点,说先垫垫,然后你倒倒时差。佩瑶把一块蛋糕塞进嘴里,说:“我一点也没有时差的感觉,咱们上街去吧?”
吴叔叔笑了,说:“随你。”
连着三天,吴叔叔请假——他在亲戚开的中餐馆里帮厨——陪佩瑶逛遍了维也纳。
景儿看过了,该工作了。吴叔叔打工的餐馆里正好缺一个跑堂,佩瑶便正式上了班。
上午11点来,晚上11点走。餐馆生意火,他们赚得自然也不少。特别是佩瑶,每天都有很多小费——长得漂亮,穿身紫红色旗袍往那儿一站,风情万种。
日子长了,难免生发浓浓的乡愁,难免有些淡淡的惆怅。吴叔叔最能为她排解寂寞了,每逢假日他们都驾车出游,雄伟的阿尔卑斯山,清澈的多瑙河,到处都留下他们的足迹。奥地利是一个名符其实的山国,他们沿着高速公路翻山越岭,火红的夕阳映在脸上,心情真是好极了!
渐渐的,佩瑶发现有一种异样的感情君临了她的心。
她有些害怕,但更多的是不安,是焦躁,是意乱神迷,是莫名的渴望和跃跃欲试的冲动。
中秋节的晚上,吴叔叔拿出朋友送的莲蓉月饼,打开一瓶红酒,又洗了些水果,两人在阳台上坐定。一瓶红酒就要见底儿了,奥地利的秋夜颇有些凉意,吴叔叔进屋为佩瑶拿披肩。刚披上她的双肩,佩瑶便突然握住了吴叔叔尚在肩头的手。
吴叔叔没有抽回。
过了片刻,佩瑶回过头来,双眼迷离的望着吴叔叔,两片鲜艳的红唇微微的张着。
吴叔叔略一迟疑,还是把自己的嘴唇贴了上去。
一发而不可收拾。吴叔叔把佩瑶抱到了床上,轻轻的除掉她的衣服,一个雪白的迷人身体展现在他的眼前——他们犯戒了。
早晨,吴叔叔坐在床沿儿,双手抱头,一声不吭。
佩瑶白嫩光滑的胳膊象藤一样缠绕过来。
“老吴。”她改变了称谓。
她爱上了老吴。她没有考虑年龄差异,没有考虑老吴的家庭状况,更没有考虑此事会给她的父母造成怎样的伤害……
老吴却不能心安。一个50岁的男人,他的道德观和伦理观都不允许他像佩瑶那样想问题。他觉得自己是在犯罪,对家庭是犯罪,对朋友是犯罪,甚至对如花似玉的佩瑶也是在犯罪。
他想中止犯罪,但他办不到——这是多么迷人的犯罪呀!
佩瑶感到很幸福。在她的眼中,老吴绝对是一个出类拔萃的男人。过去觉得他瘦的象个大虾米,现在怎么看都象米开朗基罗那些棱角分明的作品,瘦才显得精神,象一株冒雪开放的老梅;过去觉得他琐碎,现在明白正是这种琐碎显示了一个成熟男人的细心;过去觉得他老,然而只有这个年纪的男人才有一种饱经沧桑的帅气。老吴是佩瑶第一个男人,因此她无法比较床上的优劣。但她很满足,也许,与不懂事的毛头小伙子在床上的疯狂舞蹈相比,一个中年男人食髓知味的细心耕耘,更能使女孩子迷乱陶醉。
她怀孕了。
问老吴怎么办,老吴说你看呢?她笑了:“当然要生下来,这是我们爱情的结晶呀!”
老吴叹气。
孩子出世了,是个美丽的小千金。老吴为她起名叫纳纳,纪念这个孕育她的美丽城市。老吴有奥地利永久居留身份,享受奥地利国民所能享受的一切福利。因此,小纳纳的所有费用,都由奥地利政府无偿提供。佩瑶高兴的问老吴:
“这不是社会主义吗?不,简直是共产主义了!”
中国有句老话: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那还是农耕社会,如今是信息时代。两人家里都知道了老吴跟佩瑶同居生女的事。
方老师打来电话,把老吴骂了个狗血喷头!
佩瑶的爸爸打来电话,把佩瑶骂了个狗血喷头!
以至在夜里,一听电话铃响他们便在床上簌簌发抖,谁也不敢去接。
老吴的心情从此恶劣起来。他必须面对道德和家庭,一个50岁的男人,一个50岁的中国男人,精神上的负重是难以想象的。
他迷上了威士忌,经常大醉如泥的回来。
他迷上了卡西诺,经常一文不名的回来。
喝醉了酒回来,佩瑶为他端来热茶,他却粗暴地打翻在地,瞪着被酒精烧得红红的眼珠子说:“别烦我!”
输光了钱回来,佩瑶不免埋怨几句。他竟暴跳如雷,“钱是老子挣的,不用你管!”
辛佩瑶吃惊了,那个温文儒雅的吴叔叔哪儿去了?
佩瑶伤心了。当初她之所以爱上老吴,除了孤独寂寞以外,最重要的就是被老吴的成熟男子气概吸引。而现在,这种使她迷恋的气概不复存在。
那天,老吴又喝醉酒回来找茬儿,她把自己关在卫生间里哭泣。哭累了,她抬起头,不经意的看了一眼,竟发现镜子里面的女人是那样妩媚动人:眉毛弯向鬓角,光滑的额头没有一丝皱纹,眼睛又大又黑,鼻梁高高的,只是嘴巴有些大,可如今也是时尚。
再往下看,胸脯鼓鼓的。她解开睡衣,两只雪白的乳房骄傲的挺着。
难道就陪这不知珍惜的老醉鬼和老赌棍一生?
她的心突然被刺痛了。
妈妈的信接二连三的来了,劝她冷静下来,及早和老吴分手。
当老吴又又一次从卡西诺一文不名的回来时,佩瑶把妈妈的来信全部拿给他看,然后轻声说:“咱们分手吧。”
老吴慌了,扑通一声跪在佩瑶面前,说我再也不赌了,再也不喝酒了,求求你不要离开我。
4 岁的纳纳惊恐的看着爸爸妈妈。
佩瑶心软了,她扶起老吴,在他怀里失声痛哭。她想:大家都不容易,只要老吴还能象以前那样,就一块儿走到底吧。
好日子没几天。
老吴又输光了钱,垂头丧气的回来了。
老吴又喝醉了酒,摇摇晃晃的回来了。
吵闹、哭泣都无济于事。
佩瑶一横心,不辞而别,只身来到布拉格。
在奥地利干了几年,手里也有了些积蓄。她希望与过去告别,开始一种新的生活。她在布拉格注册了自己的公司,并在离地铁站很近的地方租下了一个商店,专门经营中国纺织品。她给妈妈打了电话,告诉她自己现在的情况。妈妈哭了,说孩子你做得对。快点给我寄邀请书来,妈妈要过去帮你。
妈妈来了。
她知道老吴也来了布拉格,是来找她的。她给奥地利的朋友打电话,询问纳纳的情况。朋友告诉她,老吴一见她走了,象没头苍蝇似的到处找。后来不知从哪儿打听到她去布拉格了,立马辞工,带着纳纳就奔布拉格去了。最可怜的是纳纳,佩瑶走了以后她就没笑过,忧郁极了。寸步不离老吴,生怕爸爸也没了。
佩瑶拿着电话泪珠不断。
妈妈鼓励她:“孩子,坚强些,每个人心里都有伤痛。别看现在乌云密布,走过去就是一个晴朗的天!”
当佩瑶在酒吧里对我讲述这一切的时候,她万万没有想到,老吴带着纳纳就住在离她们的家不到200 米的地方。他每天早出晚归,到处寻找佩瑶,
身心俱已疲惫至极。
辛佩瑶的生意出奇得好,妈妈帮她看店,还雇了两个捷克姑娘。她每天开车去各个批发市场找货,天天都有新货卖。
有一天下午她开车回来,巷口堵着一辆正在搬家的大货车,她不耐烦等,便从下一个巷口拐进。
她的前边有一辆福特车,她的心顿时抽紧——极为熟悉的奥地利汽车牌照映入了眼帘。
福特车在一座HOUSE前停下,头上缠着纱布的老吴走下车来。半年不见,他更瘦了,身子也有些伛偻。他背朝着佩瑶,手里拎着一袋子蔬菜。
佩瑶把车缓缓的开过去,停下,却没有熄火。老吴转过身来,一脸疲惫之色,头上的绷带有些脏了,还能依稀看到曾经渗出的血迹。
四目对视良久。
她按动电钮,车窗玻璃缓缓落下。老吴走上前来,满眼都是浑浊的泪花。
“怎么搞的?”她静静地问。
“天天到处找你,心不在焉,前天追了尾。这不,刚从修理厂取回车。”他也尽量平静地说。
“你住哪儿?”
“这儿。”他指指身后,“纳纳也在。”
佩瑶忽然泪如雨下。她后悔了,她觉得真不该扔下老吴和纳纳。
她熄了火,走进了老吴和纳纳的小屋。
纳纳见了妈妈,脸上是一副又惊又喜的表情。她扑到佩瑶怀里,大哭起来,一边哭一边问:“妈妈,你再不会不要纳纳了吧?”
佩瑶告诉我,这句话后来纳纳曾多次惊疑地问过她。她流泪了,——这是一个不到5岁的孩子呀!
佩瑶紧紧抱着纳纳,心都碎了。
老吴受伤了,还带着孩子,饮食起居都不方便,佩瑶想都没想就决定搬过来住。她匆匆回家,收拾好自己的洗漱用具,拿了几件换洗衣服,赶到店里和妈妈说清原委。
妈妈急得跳脚,说:“那是个火坑呀孩子,躲还来不及呢,你怎么非要往里跳呢!”
佩瑶哭了,说:“该跳就跳吧,这大概是命中注定的。他找我好几个月了,前天还受了伤。”
“我去见他,”妈妈火了,“我问问他还有没有起码的道德?”
“现在先别去,妈妈我求你了。”佩瑶说,“我会让他来见你的,明天就来。如果说没有道德,不是他,是我,是你女儿呀!这事儿不能怪他,他够苦的了!”
“做孽呀!”妈妈仰天长叹。
她去了。
第二天,她带着老吴和纳纳来见妈妈。纳纳乖巧的叫声“姥姥”,便坐在那儿不说也不动,象个泥塑。老吴早把脸臊得通红,垂着头说:“都是我这个混蛋,千万别难为孩子了。”
便再不吭一声。
妈妈开始流泪,又从抽泣转为嚎啕大哭。
妈妈除了接受现实,还有什么办法呢?她不愿见老吴,又心疼女儿太操劳,便把纳纳接了过来。她对我说最初一点也不喜欢这孩子,看见她就想起这一大堆烦心事儿。可这孩子是个小精豆儿,乖巧极了。特别会察言观色,从来不要这要那,也不花钱。有时给她买点零食,她都会问上好几遍:
“姥姥,真的是给我买的吗?”
“姥姥,我真的可以吃吗?”
这话听得让人落泪。纳纳虽然还不到5岁,但她已经感觉到自己生活在许多不测之中。她谨小慎微,不苟言笑,终日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如临深渊,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大难临头。
漂泊生活使她迅速成熟。
经常,佩瑶要去德国或奥地利办事。每当她在家收拾行装,纳纳都会在一旁静静地看,然后突然问:
“妈妈你还会回来吗?”
“妈妈会不会不要纳纳了?”
每逢这时,佩瑶都心如刀绞,把孩子紧紧抱在怀里,噙着眼泪一字一句的告诉纳纳:“妈妈不管走到哪里,都不会不要妈妈的妈妈和妈妈的女儿,你就放心吧。”
纳纳笑了。
佩瑶却泪流满面。
温馨的日子很快就结束了——老吴又开始在布拉格的各个卡西诺征战杀伐,烽烟四起。在维也纳的无聊故事又开始在布拉格重演,而且愈演愈烈。
佩瑶又一次硬起了心肠。
在生意交往中,她认识了一个福建老板。这是一个农民,没上过一天学。赶上改革开放的好政策,在家里开办了乡镇企业,其实就是家庭作坊,制鞋。没想到几年下来竟愈滚愈大,眼见着成了气候,腰缠亿万,旗下有十几个各式工厂。适逢国内市场疲软,便来东欧闯天下。在匈牙利、波兰、斯洛伐克都有分公司,由他的小老婆分别掌管──他的发妻在家乡守着祖宗庐墓,他纳了几个女同乡做小老婆。这老板早就垂涎佩瑶不同凡响的气质和美貌,这些都是他那些女农民不能比的。也曾半开玩笑半当真的对佩瑶说快不要一个人受苦了,过来帮我干吧,我把她们都遣散了。佩瑶斜他一眼,说:“哪儿象个老板呢,骨头没有四两沉。”
福建老板哈哈大笑,挨骂赛过吃了蜜。
要想摆脱老吴,只有离开捷克。
去哪儿呢?而且去哪儿都得有钱,有生意做。开创一个局面,花费大了去啦。她腰里不硬,底气不足。
她想起了这位福建老板。
一个电话打过去,约好在一个酒吧见面。佩瑶化了淡妆,涂了口红,在镜子里看看,忽然一阵心酸。
老板准时赶到,西服革履,还带了一束花。佩瑶接过来,说谢谢。心想这哪儿是农民的作派呢?微微一笑,把自己目前的困窘娓娓道出。
老板眼睛一瞪,“这还不容易?我找人杀了他!”
“胡说什么?”佩瑶生气了。
“那怎么办?”
“我想离开捷克。”
“去哪儿?”
“不知道。”
老板想了想,说:“我倒有个主意,你去贝尔格莱德好不好?我正想去开辟市场呢,只是苦于没有合适的人。”
佩瑶高兴了,“我去。”
“不过,”他含笑着了佩瑶一眼,欲言又止。
“骨头又轻了是不是?”佩瑶嗔道。
佩瑶悄悄地把商店卖掉,突然远走贝尔格莱德。
老吴发现佩瑶失踪了,马上赶到佩瑶的妈妈那里,大吵大闹。他知道佩瑶不会舍下纳纳,只要纳纳在,她就得回来。他命令纳纳跟他走,佩瑶妈妈说不行。他笑了,“不行?有没有搞错呀?孩子是谁的?你信不信我告你绑架?”
老吴带走了纳纳。
当晚,妈妈和佩瑶通了电话。佩瑶说你先过来吧,我已经租好了房子,纳纳的事我再想办法。
妈妈也飞到了贝尔格莱德。
安顿下来,佩瑶又悄悄回到布拉格,她准备偷走孩子。
她先在我这里住下,然后一大早就躲在老吴家附近。呆了一天也不见他出门,一直到了晚上,才见他西装革履的开车走了。
准是去卡西诺,佩瑶恨得牙根儿痒痒。
见他的车走远了,佩瑶赶紧过来摁门铃。房东笑盈盈地出来开门,见是她,高兴的用德语说:“吴先生刚刚出去。这几天你去哪儿啦?”
她胡乱应付,说刚从汉堡回来,要带纳纳出去。说罢便三步两步上了楼,推开门一看,纳纳已经睡觉了。她叫醒纳纳,孩子一看是妈妈,竟愣住了,一时说不出话来。
“纳纳,赶快起来穿衣服,跟妈妈走。”
趁纳纳穿衣服,她给老吴写了一张便条。
老吴:
纳纳我带走了,不要再找我,祝你幸福。
佩瑶
当晚,纳纳和她挤在一张小床上。
“妈妈,我们明天就走吗?”
“对,一早就走。”
“能见到姥姥了吗?”
“能。”
“纳纳可想姥姥了。”
“姥姥也想纳纳。”
“真的想纳纳?”
“真的。”
天一亮,匆匆吃过早饭,我开车带着她俩直奔机场。
然而,由于佩瑶的护照上没有纳纳的随行签证,布拉格机场海关不准纳纳与佩瑶同行。
佩瑶急了,说了一大堆好话,又把纳纳在维也纳的出生证明拿了出来,无济于事。
眼看飞机就要起飞了,佩瑶对纳纳说:“纳纳,这次妈妈怕不能带你走了。你先跟阿姨一块儿住几天,妈妈再来接你,好吗?”
纳纳真是乖巧极了,她感觉到了事情的严重性,知道自己无法跟妈妈走而必须和我呆在一起,立即开始讨好:“妈妈,我好喜欢好喜欢阿姨了,跟阿姨在一起才好呢。你放心去吧,早点来接纳纳。”
佩瑶说:“好的,你要听话,好好跟阿姨呆着,妈妈一定很快来接你。”又嘱咐我说:“拜托了,千万别让老吴把孩子找到。我回去马上办手续,争取尽快来接纳纳。”
我从她怀里抱过纳纳,说:“你放心吧,我在纳纳就在。”
佩瑶点点头,又去和海关做最后的交涉。这次她不用语言,而是把500马克夹在护照里递了进去。
事情突然就成了,纳纳被允许离开捷克。
纳纳明白了,她从立刻从我怀中挣脱,欢呼着扑向妈妈,早把她好喜欢好喜欢的阿姨扔在了脑后。
一年以后,佩瑶的妈妈来布拉格办事,我们又见面了。我问她纳纳的情况,她笑了,说:“那个小精豆儿,可不得了,现在还总问我,‘姥姥你会不会不要纳纳了?’我说你是我女儿的孩子,姥姥怎么会不要自己女儿的孩子呢?她还半信半疑。我在贝尔格莱德没事儿去练个小摊儿,也就是卖点小商品,打火机啦,发卡啦啥的。生意还不错,买的人挺多。顾客一来纳纳就帮着我卖,她德语不错,英语也能说几句。顾客都喜欢她,就买。只要一卖,她就乐的蹦儿高。说‘姥姥,真好,又卖了,真好,又卖了。’收摊儿回家,她在路上总要问:‘姥姥,咱们今天又卖了不少钱,对吧?’可疼人儿了。我们在贝尔格莱德住的房子比布拉格差远了,我就问她:‘纳纳,这儿好还是布拉格好?’你猜她怎么说?‘姥姥,贝尔格莱德真好,我真喜欢这儿,咱们就在这儿吧,哪儿也别去了。’这孩子,她是漂泊怕了。”
“那福建人怎么样?”我问。
“不怕你笑话,”她迟疑了一下,说,“你也在外边儿小十年了,外边儿的事儿都清楚。那福建人没文化,可有老婆,还不止一个。我能说什么呢?我问佩瑶你是咋想的?她说我啥都不想,就想赚钱。我试探她,问他有没有和老婆离婚的打算?佩瑶说这你怎么能问我呢?得问他呀。再说了,他离不离婚关我啥事儿?你说这还叫个话吗?不关她的事,倒好象关我的事了。这佩瑶是个孝顺孩子,看我不开心,就跟我说,妈你就别瞎操心了,他离婚我也不能嫁他,他不离婚我也不能和他分开,这道理你怎么不懂呀?还算不错,他经常往贝尔格莱德发点货,利润对半分。刚去时钱不够用,他也帮助了一些。隔一两个月他去一次,呆个十天八天的,看看销售情况,考察考察市场。唉,真是斯文扫地呀。话本小说上不是常有这么两句吗?明知不是伴,情急也相随。”
她要回贝尔格莱德了,我送她去机场,把一包东西交给她,说:“全是吃的,昨天国内来人捎来的。都是什么话梅、应子、牛肉干儿,给纳纳和佩瑶吃。”
一天晚上,我正和几个朋友在酒吧嗨,电话响了。是佩瑶从贝尔格莱德打来的。
简单的问候之后,她告诉我塞尔维亚不能呆了,政府对中国人的刁难和歧视已经让人无法忍受,她准备最近就带着纳纳和妈妈离开。
我问她要去哪里?她说还没有最后决定,但已经有了两个目标,一个是科特迪瓦。我一时懵住了,问科特迪瓦在哪儿?她说是非洲西部的一个小国家,以前忘了是叫黄金海岸还是叫象牙海岸。
另一个呢?我问。
另一个是柬埔寨。她说。
我不明白你去柬埔寨干什么?我说。那里连地雷都没挖干净,满街都是一条腿儿蹦的人。非洲也不能去,那儿的蚊子听说比麻雀都大,你是不是脑子有毛病啦?
她说没办法,只有这样的国家不歧视中国人。
我说我知道有一个国家,她最适合你去,而且保证不会受到任何歧视。
她说世界上会有这样的地方吗?你快告诉我是哪个国家。
“CHIN。”我说。
她迟疑了一下,说:“不,我回不去了。你别劝我,我知道你是为我好。我就不信这个世界没有我立足的地方。别替我担心,到了新地方我会打电话给你的。
我哭了。